张泽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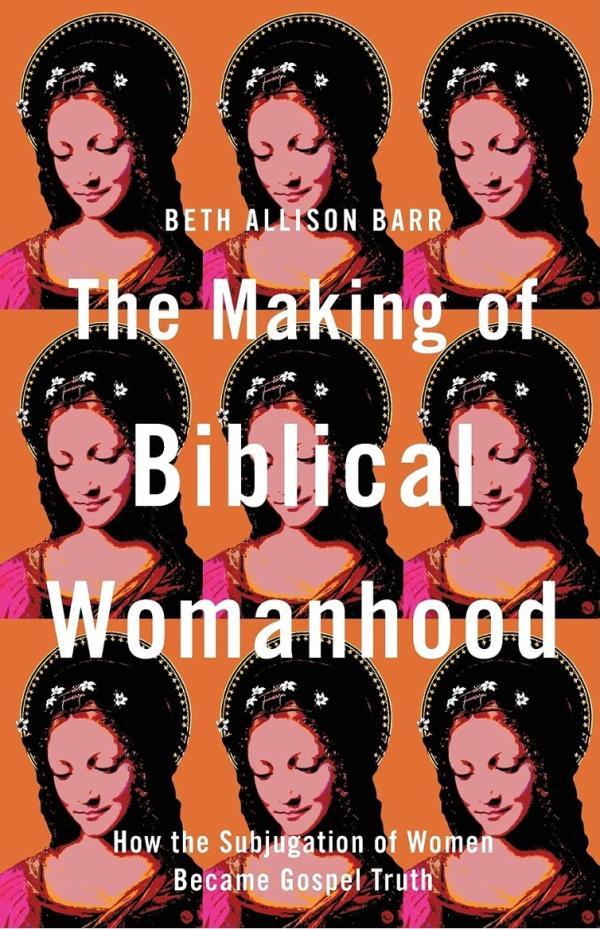
Beth Allison Barr, The Making of Biblical Womanhood: How the Subjugation of Women Became Gospel Truth, Brazos Press, 2021
近年来,以#MeToo运动为代表的性别平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得如火如荼,在美国较保守的基督教教会内部也产生了可观的震动。此前,对于性别问题,美国基督教徒,特别是福音派与改革派信徒,持有的主流立场是“互补神学”(complementarianism),即认为上帝在创世时赋予男性与女性不同的角色,男性天然应是领导者。保罗书信中强调女性从属地位的篇章是互补神学家最常引用的经文证据,其中最著名的是《以弗所书》中的一段:“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5:22-24)从字面上看,我们似乎难以否认保罗笔下的女性从属于男性,但这是否就是源于《圣经》的真理呢?自保罗以下的教会是否一向强调女性的从属地位?世俗世界的性别平权运动激励着基督徒学者不断反思传统神学在性别问题上的立场。
贝思·艾利森·巴尔的新书《“圣经女性身份”的形成》从教会史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追溯互补神学的起源,并对其进行批判与反思。此书发行后十分畅销,曾在亚马逊图书榜排到前一百名,在美国基督教学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作者巴尔拥有双重身份,既是历史系的中世纪史教授,又是一名浸礼会牧师的妻子。在本书导言中,她真诚地向读者讲述了自己创作此书的缘由。巴尔从小接受南方浸礼会的宗教教育,前半生一直持互补神学立场,即认为上帝在创世时便意在让男性主导,让女性服从。直到五年前,巴尔的丈夫因为主张女性可以在主日学校给男孩子上课而被教会解雇,这一打击使巴尔开始反思自己在性别问题上的信仰。在本书中,她力图通过自己对《圣经》与教会史的研究证明压迫女性的互补神学并非源于《圣经》的神圣权威,而是历史的产物,并且在神学上站不住脚。

贝思·艾利森·巴尔
让我们再次回到保罗书信。在本书第二章开头,巴尔列举了七段保罗书信中的相关经文(其中,《以弗所书》5:21-6:9、《歌罗西书》3:18-4:1、《彼得前书》2:18-3:7和《提多书》2:1-10被合称为“家庭规章”),其侧重各有不同,但都强调女性应服从男性的权威,因此向来被持互补神学立场的信徒视为确凿的证据(我曾经和浸礼会学校的朋友说起女性在教会布道的问题,朋友当即引用保罗书信的经文,称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违背圣经的”,可见这种立场相当普遍)。巴尔从《圣经》经文与历史背景两个角度重新审视了保罗书信的这些段落。以《以弗所书》第五章为例。首先,在历史上,父权制是罗马帝国的社会现实,女性在财产与法律方面受到父亲、丈夫或男性近亲的监护,因此保罗关于妻子服从丈夫的表述反映了罗马的历史情形。但在此之上,保罗旋即强调了丈夫对妻子的义务:“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5:25)巴尔指出,虽然今日的读者会觉得强调妻子服从的部分刺耳,但当时的罗马读者可能觉得强调丈夫义务的部分更为突出。保罗甚至要求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以弗所书》5:28),而罗马社会的主流思想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在《论动物的生成》中的观点,即认为女性的身体相比于男性是畸形而有缺陷的。可见,在罗马父权社会的背景下,对当时的读者来说,保罗书信相关篇章的侧重并不是女性的服从。
其次,经文的翻译也影响着读者的理解。《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要求妻子顺服丈夫,而前文第二十一节则要求所有人都“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如将两节对读,就能看出妻子的顺服只是信徒彼此顺服的一部分,而第二十一节的要求对丈夫同样适用。但在英文标准版圣经(ESV)中,第二十一节被划归在上一个小标题中,而“妻子和丈夫”这一小标题则以第二十二节开始,这种分段方式无疑支持了互补神学的立场。另一个受到翻译影响的例子是罗马书第十六章所列举的大量在教会服务的女性,其中非比(Phoebe)的职位(διάκονος)在某些译本中被译为正式的“执事”(deacon),而在另一些译本中被译为非正式的“仆人”(servant)。巴尔指出,如果非比是男性,则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争议。而单从经文本身来看,保罗并不持有压迫女性的立场。
通过对保罗书信相关章节的重新解读,巴尔质疑了互补神学的经文依据,而在第三章,巴尔列举中世纪教会史上杰出的女性典范,进一步说明互补神学所谓的正统“圣经女性身份”(Biblical womanhood)只是较晚近的历史建构,在中世纪时期还未曾确立。虽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称“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14:34),但中世纪的女性并不曾沉默:面对约克大主教的发难,玛格丽·坎普(Margery Kempe)勇敢地捍卫了自己谈论上帝的权利;圣保拉(Saint Paula)抛弃了自己的家庭,远赴伯利恒,帮助圣哲罗姆翻译《圣经》;宾根的赫德嘉(Hildegard of Bingen)曾四次远行布道,主教们争相索要她的布道词。然而,自十一至十二世纪以降,为了保持独立,防止豪门世家的过度干预,教会开始要求神职人员必须独身,视女性的身体为不洁的威胁。由此,教会得以在世俗权力面前保持独立,但女性的地位逐渐被削弱了。
总体而言,中世纪的教会并没有禁止女性发声:仍有少部分女性可以通过守贞与卓越的品质成为例外。但这些例外很快便消失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真正为当代互补神学压迫女性的话语奠定基础的,是以揭露天主教会的黑暗与腐败为己任的宗教改革运动。巴尔在第四章中指出,虽然女性在任何时代都扮演着妻子与母亲的角色,但是将这种角色视为女性神圣性的标准,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的。婚姻与母职取代了贞洁,成为女性的理想圣洁状态;丈夫取代了神父,成为女性应当服从的权威。以路德本人为例:相比于圣母玛利亚和其他女性圣徒,路德更强调拉撒路的姐姐马大(Martha)打理家务的美德。被限制在家庭中的女性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在十五世纪初,当约克主教企图引用保罗书信来让玛格丽·坎普闭嘴时,坎普仍能引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中和耶稣对话的女性为自己辩护;但到了十六世纪,安·阿斯库(Anne Askew)以相似的论证反驳试图压制她的主教,却最终被处以火刑。
随着新教教会进一步束缚与压迫女性,保罗书信中的相关篇章的地位迅速上升,而对这些篇章的解读也有了与中世纪时期完全不同的侧重。保罗书信是中世纪布道者最常引用的《圣经》经文之一,然而在巴尔研读过的一百二十个晚期中世纪布道词手抄本中,只有个别几段用到了与性别问题相关的段落,而其用意也不在于论述女性的地位。《以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为例,经文称女性“必在生产上得救”。巴尔仅遇到两篇谈论这段经文的中世纪布道词,其中之一以女性为所有基督徒的代表,强调所有基督徒都要经历痛苦的忏悔与赎罪,才能享受救赎的快乐。与这种平等的解读形成对比的,是十七世纪著名神学家兰斯洛特·安德鲁斯(Lancelot Andrewes)对这段经文的解读:“维护家庭的义务属于女性……如保罗在《提摩西前书》2:15中所说,妻子通过孕育孩子获得拯救。”由此可见,在宗教改革运动后,人们才开始将保罗书信用于定义基督教女性角色。此外,女性角色在这一时期的转变还体现在教堂的格局布置上。在中世纪的教堂的礼拜仪式中,男性与女性分列两侧,而在宗教改革后的教堂,每个家庭占据一个独立的格子(box),女性的声音自此淹没在家庭这一最小单位中。
宗教改革运动的重要成就之一是俗语《圣经》的普及。在新教信仰的“五个唯独”原则中,“唯独《圣经》”居于显要地位,而对女性的压迫也同样体现在新教徒对《圣经》经文的翻译中。在本书第五章,巴尔展示了不同时代的英语《圣经》对性别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新国际版《圣经》(NIV)因其性别中立的语言受到批评,保守派神学家称世俗世界的女性主义潮流歪曲了《圣经》经文,而2001年发行的英文标准版《圣经》(ESV)则拒绝使用这种性别中立的语言,是对女性主义自由派的直接回应。作为中世纪历史学者,巴尔指出《圣经》语言的性别中立问题并不是现代女性主义潮流的产物,而是古已有之。首先,巴尔纠正了一个普遍的错误认知:俗语《圣经》的阅读并非始于宗教改革。通过布道词中对经文的翻译,中世纪的平信徒很早便能广泛地接触《圣经》经文,而这些布道词中的经文翻译往往采用性别包容的方式。以《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七节为例(“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巴尔指出,对“人”这个字,希伯来文的’adam和拉丁通俗译本的homo都是性别中立的“人类”,而在很多中世纪布道词中,为了强调性别包容,这句经文被译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巴尔还举出其它几段经文,其中在现代译本中被译作man的字常常在布道词中被译作man and woman,可见这种性别包容的译法并不是现代女性主义的产物。但这种译法在宗教改革后不再流行,而十七世纪的英文钦定本《圣经》(KJV)更是着意强调女性作为妻子的家庭角色。希伯来文《圣经》中的“女性”一词既可以指一般的女性,也可以特指妻子;由于英文中相应的词并没有这种双重义,在钦定本《圣经》中,“女性”一字常常被不恰当地译作“妻子”,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的家庭角色。自此,女性通过守贞保持圣洁的方式被《圣经》经文彻底否定:在钦定本《圣经》中,上帝创世时,女性的角色就是“妻子”。
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同样具有讽刺性的,是启蒙运动时期近代科学对女性角色的禁锢。以进步自居的启蒙运动在性别问题上却愈发保守:如果亚里士多德笔下的女性是男性畸形而不完美的版本,那么启蒙思想家则认为男女的性别差异是本质上的不同,女性在生理上更接近于幼儿,并不能胜任对真理的追求,只适合打理家务。这种观点得到了同时代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扩张的支持:当机器为包括女性在内的工人阶层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时,资本家却坚持给女性工人支付比男性低得多的工资,以此限制女性外出工作。十八至十九世纪的历史进一步证明,女性从属于丈夫的观点完全是历史的产物。
在世俗历史之外,巴尔也利用美国福音派基督教自身的历史和神学来批判互补主义神学的荒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虽然社会主流观点认为女性的主要职责是家务,但令人惊讶的是,仍有数目可观的福音派女性基督徒在教堂讲道,有些女性甚至因此出名,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至于有学者称,女性履行牧职是福音派基督教的传统特色,正是由于福音派基督徒对经文本身的重视超过了世俗意见对他们的影响,他们才能够接受并支持女性在教会公开讲道——这样的论点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充满讽刺的。在巴尔看来,那些如今持互补神学立场的人已经忘记了福音派基督教的历史。不过巴尔也指出,二十世纪公开讲道的福音派女性和中世纪时以玛格丽·坎普为代表的女性仍有很大不同:前者仍不能违背男性的权威,不能像中世纪的杰出女性一样超越自身的性别——讲道只是她们在家庭主妇之外的“副业”(side gig)。
自此,巴尔追溯了自保罗时代到二十世纪的基督教女性地位的流变,充分证明互补神学的父权立场并不是不可反驳的福音真理,而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是社会变革、经济与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之上,巴尔进一步指出互补神学的性别观在神学上的谬误,完成她对互补神学的最后一击。在世纪之交,历史上著名的阿利乌主义(Arianism)在福音派基督徒中竟有重萌的趋势,一些人甚至提出,因为耶稣永远从属于圣父,所以妻子永远从属于丈夫。他们将三位一体中的权威与服从关系视为互补神学的依据,并由此宣称女性讲道违背了基督教正统,却不知圣子从属于圣父的观点才是违背基督教正统的确凿无疑的异端(heresy)——325年的尼西亚公会正式将阿利乌主义定为异端,确认在三位一体中不存在等级。我们不难想象,将阿利乌主义用于论证互补神学十分方便有力,但不容忽视的是,即使是无意为之,在捍卫女性天然应当从属于男性这种原本就站不住脚的立场时,互补神学家竟然荒谬到援引早期教会史上最著名的异端,不惜背离正统的信仰。巴尔犀利地指出,互补神学所持的以服从为主的“圣经女性身份”已经开始损害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自古以来,基督徒便以“出淤泥而不染”的处事态度自居,信奉“活在世间,但不属于此世”的准则。这一原则也被互补神学家用以反驳世俗世界的女性主义思潮。但巴尔代表了基督教神学领域支持女性平权运动的声音。本书通过扎实的历史研究与犀利的神学论证有力地批判了互补神学的立场,充分揭示了强调服从的“圣经女性身份”的历史性,证明这种压迫女性的父权神学不仅不是基于《圣经》的真理,而且恰恰体现了基督教难以逃脱世俗影响的一面。如本书第一章中所说,基督教的父权和世俗世界的父权是高度一致的,它并不是上帝的本意,而是人类原罪的体现。若当代基督徒能真正做到不落世俗的窠臼,遵循神的教导,则应首先还女性以自由。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施鋆
原地址:https://www.chinesefood8.com/12251.html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上一篇:圣经中魔鬼总共有多少个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