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凭借“文情俱胜的随笔”(周作人《文载道文抄序》,收入《立春以前》,太平书局,1945年)在文坛崭露头角,随后却突然沉寂多年,仅以古籍整理编校为业的金性尧,从1982年开始应邀在《书林》杂志上陆续撰文讲说古典诗歌。专栏取名为“炉边诗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清初诗论家吴乔那部有名的《围炉诗话》,不过两者的境况其实大相径庭。吴著是和诸多志同道合的友朋欢谈切磋的产物,众人“围炉取暖,噉爆栗,烹苦茶,笑言飚举,无复畛畦”(《围炉诗话自序》),充满了不拘形迹、往还商讨的热闹气氛。相形之下,金性尧就凄清落寞得多,正如他此后在将这些随笔汇集成书时所说的那样,“因为写时在冬天,室内有一只取暖的炉子,便随手取了这个名字”;回忆起那数年撰稿的时光,他更是出人意料地感叹,“对于去日苦多的老人来说,这六七年却不同于少壮时代的过程,就像每天撕下一张日历,薄薄一张纸,撕一张就少一天了”(《炉边诗话·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竟然显得黯然神伤而意气消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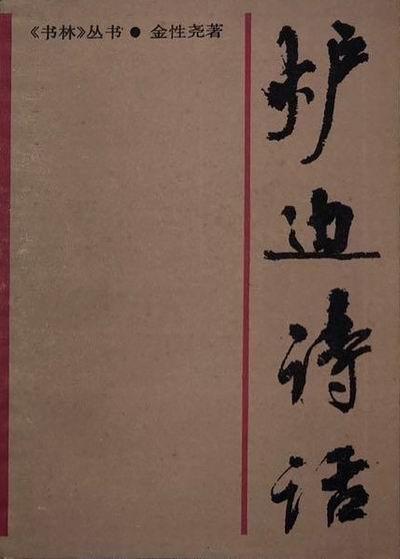
金性尧《炉边诗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好在一旦谈起诗,金性尧立刻又恢复了神定气闲、挥洒自如的风采。这些说诗随笔所涉甚广,上起先秦时期的《诗经》,下至清末戊戌六君子中的林旭。从中固然足以展现其深厚丰赡的腹笥,而更值得反复体味的则是那些平实通达却屡有新意的见解。在《杜甫写马》中,他极力表彰前代的批评家,“凡是评论到杜诗中精采作品,这些评语也往往神采飞扬,表现出他们高超的欣赏能力,一看到杜诗中‘死不休’的名句,他们的审美敏感就一触即发,和诗人一样表现出他们的能动性。即使是寥寥数十字,也不失为杜甫的钟子期”,倒是很有些夫子自道的意味。即便是耳熟能详的诗篇,听他从容不迫地娓娓道来,也同样能引人入胜。比如在《贺知章还乡》中论及《回乡偶书》,他先引杜甫《遣兴五首》其四中的“贺公雅吴语”,来作贺诗“乡音无改”的注脚,笔锋随即顺势一转,提到“人的乡音是很难改变的,往往与生命相终始。想起来,他和讲四川话的李白,讲河南话的杜甫以及长安人谈话,一定很吃力”,就这么闲闲散散地扯出几笔,却涉笔成趣,大有知堂散文的余韵。最后他又归结全篇宗旨:“诗里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感伤或激动情绪,而是不多不少、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一个老人的今昔之感。在长安时,只能从怀念中、梦境中萦绕的故乡的一堆土山、一条游鱼,现在都重新回到了眼前。尽管时间已从他脚下脉脉地流过了几十年,他却还能拾起时间的残片,让过去和现在联缀着;尽管时间已经改变了故乡的许多事物,这些事物却永远不会在老人记忆中消失。就在回乡这一年,老人终于和镜湖的水色诀别了。”曲终人散而余音袅袅,这种看似平淡冷静实则低徊怅惘的思乡之情,仿佛模糊黯淡却又清晰明亮的记忆碎片,恐怕也是他逐渐迈入暮年以后的真切体验。正因为掩卷冥思时感同身受,所以铺纸落墨之际,就能指引读者仔细品咂其中的复杂滋味。

晚年金性尧
在回顾自己的读书经历时,金性尧自陈“我没有理论分析的能力,只知道作家的创作实践”(《夜半钟声到客船》,收入《不殇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年轻时丰富的创作经验确实令他对个中甘苦体会极深,所以在赏奇析疑时特别擅长从细微处着眼,仔细涵咏玩索旁人不经意的地方。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他对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所作的分析。这首诗明白如话,最后一句“风雪夜归人”尤其脍炙人口——现代剧作家吴祖光甚至信手拈来,直接将其作为自己剧本的题名——似乎无待辞费再予深究。不过,这个“人”究竟是指谁?绝大部分读者或许想当然地认定是那位投宿者,也就是诗人自己。当年流传极广的《唐诗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在串讲时,就说是“风雪夜晚的行人像是回到家里一样呵!”金性尧参与过该书初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的编选注释,虽然没有承担此后的增删修订,但对此类意见想来应该早有耳闻。然而他在《风雪夜归人的“人”是谁》中却另有设想,“夜归人恐非指诗人自己”。最初在杂志上发表该文时,他就质疑道:“为什么不说风雪夜行人而说风雪夜归人?正是一个针对性的眼子,因为旅途投宿似很难说‘归’。”从诗人的遣词造语来推敲琢磨,通行的意见确实有些扞格难通。而他并未就此罢休,又兴致勃勃地搜集钩沉相关文献,发现宋人陈师道的五律《雪》中有“寒巷闻惊犬,邻家有夜归”之句,应当是自刘诗脱化而来,“似也理解为犬是白屋以外之犬,‘归’是邻人之‘归’”。与此同时,他还介绍了同事兼友人陈邦炎的看法,“把夜归人解为芙蓉山主人自己”。可他并不认同此说,“我的意思不如解为不相干的村人夜归”。稍后不久,他又读到清人黄叔灿在《唐诗笺注》中的相关论说,尽管语意稍嫌含混,“似乎也把夜归人理解为别人(芙蓉山主人?)而非诗人自己”。他据此进一步推论,如果这个“人”的确“是指芙蓉山主人,那么,更有可以共语之人了”,修正了自己先前的主张。他对这篇随笔很满意,多年后还将其抽出,另行编入自选集《一盏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内,并新增补记一则,除了征引明人唐汝询《唐诗解》中的评说以供读者参考之外,再次强调:“究竟指谁,现在当然还不能肯定,能够肯定的只有这一点:刘诗‘风雪夜归人’的‘人’不一定指诗人自己。重复说一句,这个‘归’字非泛语而为定语,实为归家之归。”前前后后虽然只是围绕一个字研讨,他自己也有些举棋不定而左右游移,以致最终并未做出确定无疑的判断,却曲径通幽般带领着读者感受到诗人造境的荒寒幽渺以及落笔的深细不苟。
有时金性尧还能综合考察各方面的因素,设身处地去探究诗人的创作主旨,由此廓清种种误读歧解。比如提到陶渊明,人们往往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他在归隐后便悠游自在,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一般,就像鲁迅曾经调侃揶揄过的那样,“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题未定”草(六)》,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然而追根究底一番,大概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读者,陶渊明本人恐怕也“难辞其咎”。正是他在不少作品中反复渲染宁静祥和的田园生活,才导致后世逐渐形成了这种不无偏颇的印象。金性尧在《陶渊明田园诗》中对当时的社会背景多有介绍,但他并不满足于揭示“陶渊明时代的农村当然极其残破黑暗,天灾人祸绝不会放过它”,并就此责备诗人有“美化现实”之嫌,而是紧接着追问为什么在其创作和现实之间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反差。在他看来,“作为诗人的陶渊明是在写诗,诗总是倾向美的”,“因而在写他的周围世界时,总是要把注意力主动地集中在能使他得到稳定、和谐的快感的对象上,并把它们驯服于自己的欣赏趣味上来完成”,“因而一些与此相反的杂质也就被剔除,如同他写‘野老’时总是写他淳朴可爱的一面”。他并没有受到“文学必须反映现实”之类教条的束缚,而是深入探析诗人曲折隐秘的创作心态,对这种看似不符常情的现象就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另一篇《杜甫与李白》中,他提到杜甫《春日忆李白》中有“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之句,用六朝诗人庾信和鲍照来比况好友,前人对此聚讼纷纭,有的甚至联系到诗中另两句“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认为这是老杜的微词婉讽,“暗示李白不要局限于庾信、鲍照,而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对此颇不以为然,除了指出用“清新”“俊逸”来形容三人的创作风格大致适用,并没有比拟不伦的弊病外,尤为强调“杜甫是唐代中叶的人,唐诗是从六朝诗发展过来。他要举前代名家的榜样,也只能举些庾鲍、阴何、二谢之类”,“我们看看阴何之类,实在不过尔尔,但在杜甫那个时代,他举阴何、庾鲍等,便是最高的典范了”,所以诗中所言“完全从推崇他的善意出发,没有丝毫‘微词’用意”。杜甫在品评时能用来比勘参照的主要是六朝诗人,在那样一个自成统序的创作谱系中,庾信和鲍照无疑都是超迈同侪的杰出代表。后人当然可以将他们置于承传递嬗的诗史源流之中,通过和唐宋以降历代名家的比较,重新评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绝不能以这种“后见之明”来对前人求全责备,甚至以今度古而妄加评议。
历代的诗话、笔记中有大量论诗衡艺的精彩片段,金性尧在评说中也时常引录参酌。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各种不循常规的异见——有些甚至可以称作偏见乃至谬见——并不轻率地鄙薄或排斥,而是体现出充分的尊重和体谅。在《陶渊明田园诗》中,他提到晚清学者钱振锽对陶渊明的指摘,批评陶诗“美不掩恶,瑕胜于瑜,其中佳诗不过二十首耳。然其所为佳者,亦非独得之秘,后人颇能学而似之”,措词相当刻薄尖酸。他对此非但不以为忤,还相当欣赏,强调“他说得是否完全正确,是另一问题,但这种多少带些‘异众’精神的立论,却是应该用青眼来看的。在学术上的诺诺连声的时候,何妨有寥落的谔谔之声呢”。他后来在《“不素餐”解》(收入《伸脚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中介绍过孟子对《诗经·伐檀》篇“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两句的解释,也曾借题发挥道:“对孟子的说法,有的人根本不赞同,那倒不失为旗帜鲜明的态度;有的人是赞同的,却不敢公开表达,与其谔谔,不如诺诺,倒真是学术上的素餐者了。”足见他对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之辈充满了厌弃反感,对不拘成说、另辟蹊径者倒是刮目相看。

金性尧《伸脚录》
当然,这种对待不同意见的异量之美绝不是毫无原则的放任纵容,终究还得看立论者究竟是在坚持独立思考抑或仅仅为了标新立异。比如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对杜甫《古柏行》中“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两句有过非议,认为真如诗中所言,那么这棵参天大树“无乃太细长乎”?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辑录过宋代以来的不少评论,对此多有斥责辩驳,异口同声都认为不可信从。金性尧在《夔州古柏》中虽然也指出沈氏“以物理学角度来衡量艺术品”,不免有些迂阔拘泥,“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当然要注意细节,但个别细节上的真实毕竟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作品”;不过他随后又郑重其事地补充说,“尽管我们对沈括评杜诗这一具体论点不敢苟同,但他的科学的求实求证精神倒也未可厚非”,“常识或理性也并非完全是诗词的蛇足,就看他们如何运用”,“如果说,他们的思想方法近乎钻牛角尖,也还是规规矩矩地从学术的牛角里钻去,毕竟不同于庸俗低级、哗众取宠那种论调”。如此体贴入微的阐发商榷,毫无疑问比简单粗暴的讥评嘲笑更能令对手心悦诚服,也更能促使读者平心静气地沉思回味。同样是围绕杜诗的研读,他在《杜甫与李白》中说起杜甫因关切李白安危而感慨“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指出“所谓杀,只是极言当时对李白排挤打击的厉害,并非真要杀他”,而从杜诗来看,两人交谊深厚,“他才是李白的死生知己”。随后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到郭沫若那部因为善于揣摩上意而得以显赫一时的大作:“可是在《李白与杜甫》中却这样说:‘但他(指杜甫)只怜李白的才,而不能辨李白的冤;在他看来,李白仍然犯了大罪,非真狂而是“佯狂”,应该杀而不杀,如此而已。’”尽管对此未着一字评议,可褒贬之意显然已呼之欲出了。
金性尧不仅对前人的谔谔之言青睐有加,在评说诗文的过程中也身体力行,就像他后来所说的那样,“看到古书中的话有同意的,就想附和发挥,不同意的,就想纠正评议”(《夜半钟声到客船》,收入《不殇录》),某些意见乍闻之下甚至还颇为刺耳。在《吴中四才子唐寅》中,他谈到《红楼梦》中有些诗词或许受到唐寅的影响,就突然插入这么一段:“在古典小说中,《水浒传》中的诗远胜于《红楼梦》中的诗。《红楼梦》中有好多首确使人感到庸俗,《水浒》诗却俗得质朴自然,如宋江在浔阳楼题的‘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反诗,就颇有草泽英雄本色。”相同的意见在另一篇随笔《〈章太炎全集〉何时全》(收入《不殇录》)中也捎带提到过:“若就诗论诗,要推宋江的那首‘敢笑黄巢不丈夫’最有气魄。《水浒传》中诗的数量不及《红楼》多,水平却高出于《红楼》。”可知这绝不是一时兴起的随口漫道,而是蓄积于胸不吐不快的由衷之言。红学家们听了这番话想必会皱眉蹙眼,其实大可不必。艺术鉴赏本就是见仁见智,言人人殊,最能够也最应该充分彰显批评家的独特个性。更何况小说家替笔下的各色人等操刀代笔,自然力求惟妙惟肖,以契合各自不同的身份,其实并不能直接反映他本人诗才的高下。批评《红楼梦》中的诗作不佳,归根结底并不意味着贬低曹雪芹和《红楼梦》。类似的议论在书中屡见不鲜,如指出潘岳的《悼亡诗》“落了鹣鹣鲽鲽的俗套(虽然这四个字可能出现在潘诗之后),而且近于文字技术上的卖弄。至哀极痛,雕饰过甚,反失本性”(《潘岳悼亡》);批评林逋的梅花诗“结句平弱,局部和整体不相称,境界狭窄,笔法纤巧”,“身为高士,却又诗多浮文俗句”(《孤山梅花》);认为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部分篇章“不仅艰涩难懂,为了求奇,却流于怪僻,缺少诗味”(《九州生气》),都直言不讳而一针见血。在他而言自然有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读者从中也不难感受到脱略俗套的坦率真诚。

金性尧《不殇录》
在修改润饰这些随笔时,金性尧坦言:“由于应约写稿,只是想到就写,所以杂,所以乱,也谈不上什么‘体系’。”(《炉边诗话·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当然不无谦退之意,可是有些篇目的选定确实有些不同寻常而耐人寻味。比如在《韩愈贬潮州》中,除了介绍《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题楚昭王庙》《祭鳄鱼文》等历来传颂的名篇,他还特意讲说了《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留题驿梁》和《女挐圹铭》这样很少受到前人关注的作品。韩愈回想起受到自己牵累而不幸早逝的女儿,忍不住痛彻心扉而老泪纵横。金性尧在分析讲解中也常常深怀悲悯而情难自已,述及韩家诸人无端遭受株连,不禁义愤填膺说“父亲犯罪,却连十二岁的患病女儿也不准留在京城”;讲到数年后韩愈将女儿尸骨移葬回故乡,忽然提及“古人结婚早,如果这时她还活着,也快到出嫁之年了”,对亡者的孤苦凄凉唏嘘不已;说起韩愈去世,又自问自答道“不知这对父女能否在地下重逢?也但愿他们能够重逢”,对缥缈难凭的九泉重逢逢竟然也满怀期盼。这篇随笔经过剪裁修订,又被他收入《夜阑话韩柳》(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和《闭关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两书。前者改题为“一人做事一家当”,悲愤痛切之意更为明瞭显豁;后者改题为“韩愈祭女”,则隐隐透露出这位正当豆蔻年华却不幸凋零早徂的少女才是他关切的焦点。寻绎推究金性尧撰写这篇随笔的初衷,恐怕与其长女的含冤辞世密切相关。追溯此事的原委曲直,简直荒诞无稽到令人毛骨悚然。仅仅因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而且“她本人通晓俄语、英语,读了一些十九世纪的西洋文艺作品”,“对事物敢于独立思考,努力使大脑变得有用,自然也有些锋芒和棱角”,年轻的女孩就莫名其妙遭受到无妄之灾,成了“在劫难逃的‘白专’典型”,并在怀孕两个月的情况下,被“当作‘阶级斗争’的反面教材来‘教育群众’”。在缕述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金性尧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然而说到女儿最终不堪受辱而服毒自尽,“席子上沾着她呕吐过的痕迹,说明她死前经过痛苦的磨折,她也许在阴间还在挣扎”;即便如此,“都要被鞭尸”,“差一点就是咎由自取了”(《她才二十八岁》,收入《伸脚录》),他还是忍不住悲愤交加。即使时隔多年,这些事依然不能淡忘,“有好多留下了隐隐作痛的伤口”,“人们都知道黄连很苦,然而只有尝过黄连的人才深知其苦味”(《找寻》,收入《伸脚录》)。正因为有着同样惨烈苦痛的回忆,他对韩愈笔下的琐屑家事才会深有感触,并借着分析解说的机会稍抒内心的抑郁愤懑。因此,尽管他在文中说,“这样的事例,对今天的人来说,是万难相信的,在韩愈时代,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韩愈贬潮州》),大概还是别有言外之意,未必真作如是想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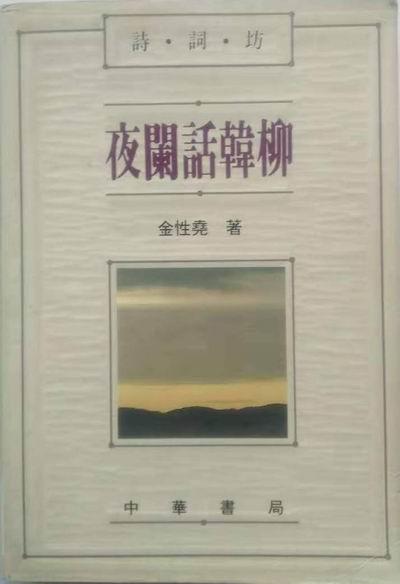
金性尧《夜阑话韩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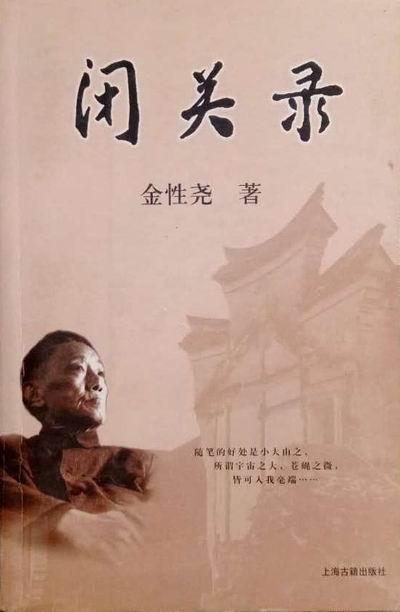
金性尧《闭关录》
汇编结集后的《炉边诗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不仅纸墨粗劣不堪,印数也只有寥寥三千册,流传并不广。金性尧生前曾计划将这部旧作“增订一遍”,“可是纸墨摊开之后,一见老花镜就气沮了”(《滥竽录》,收入《闭关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经过改订润饰,收录在他的另几本随笔集中。几年前曾见有新版《炉边诗话》(中西书局,2011年)行世,在删去部分篇章后号称“精选本”,其实所收其余各篇均一仍旧貌,并没有吸收作者后来所作的修订补正(如上文提到过的,《风雪夜归人的“人”是谁》在收入《一盏录》时新增过一段附记)。最近又见到另一新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付梓重印,尽管篇目并未删减,可经作者修正过的内容仍告阙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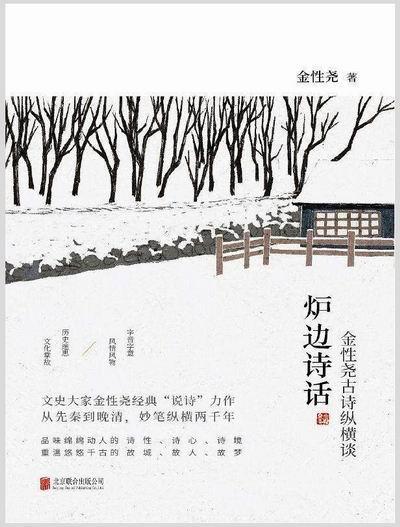
金性尧《炉边诗话》,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
不但如此,出版者还越俎代庖地替原书添加了大量注释。比如在《前言》一开篇,金性尧自谦道:“这是一件百衲衣,也是从杂家铺子的零缣残帛中拾来的。”编辑就特别提醒读者注意这个“缣”是指“细密的绢”,实在令人有些啼笑皆非。想到金性尧曾经感慨过,“一首诗、一部书的读者的质比读者的量要重要得多。这话原不新鲜,只是有时候便成为‘不现实’”(《〈无题〉诗中男性的女性化》),真叫人不由得废书而叹。
原地址:https://www.chinesefood8.com/16378.html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