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现象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上映,影片改编自刘慈欣的同名小说,该小说首发于2000年第6期
全文共5954字,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
更早的1994年,也是三百年一遇的大型彗星将与木星相撞的那晚,谭楷记得那天很冷,他们还租了军大衣御寒。许多人为了用小小的天文望远镜看一眼星空,在峨眉山金顶排起了长队,这让谭楷很感动:“只要一个民族还有好奇心,还能仰望星空,这个民族就有希望,就还能搞科幻。”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刘悠翔
南方周末实习生 陈亚杰
责任编辑 | 邢人俨
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中,1979年,人类第一次读到了来自宇宙中另一个世界的信息。中国天体物理学家叶文洁不顾警告,向外星文明发射了回信。人类与外星文明首次对话。
现实中的1979年,几个中国人在四川成都创立了《科学文艺》杂志(注:更名于1991年的《科幻世界》的前身),开始了探索科学、未来与未知的旅程。
四十年间,《科幻世界》留下过许多惊人的预言——
《科幻世界》的明星作家韩松,在2000年出版的小说中描写了美国世贸中心未来遭炸弹袭击和飞机撞击的情景。一年后的9月11日,美国世贸中心遭遇恐怖袭击。在这部小说中,韩松还写到未来西方金融体系的崩溃,以及中国启动应急体系幸免于危机,类似的情节在2008年真实发生,持续至今。
1999年第7期《科幻世界》刊登了关于记忆移植的文章《长生不老的梦想》和小说《心歌魅影》。杂志上市一周后的全国高考,作文题赫然印着“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届高考考生郭帆和龚格尔是《科幻世界》忠实读者,他们因此受益。2019年,郭帆导演、龚格尔参与编剧的现象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上映,影片改编自刘慈欣的同名小说——这篇小说也诞生于2000年第6期的《科幻世界》。
科幻作家王晋康从1993年开始在《科幻世界》持续发表有关基因编辑的小说。2018年11月,基因编辑婴儿在深圳诞生。消息传来时,王晋康刚刚在深圳过完70岁生日,陪在他身边的是《科幻世界》的编辑们和作家们。
作为中国唯一一份延续至今并从未停刊的科幻杂志,《科幻世界》从1990年代中期起就成为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
《科幻世界》的四十年,也是中国科幻的四十年。
“我们要是停刊了, 中国科幻就没人搞了”《科幻世界》最初并不主打科幻小说,1979年创刊时取名《科学文艺》,办刊宗旨是“以文艺的形式普及科学知识”,沿袭连苏联都弃之不用的1930年代科普作家伊林的口号。《科学文艺》创刊号上的12篇文章中,只有两篇是真正的科学幻想小说。
当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科幻小说并不等同于“普及科学知识的小说”。1981年,对科幻小说的质疑渐渐出现。许多科幻小说的情节是当时科学无法证实的,作家因此遭到批评。比如叶永烈的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写过,科考队在珠穆朗玛峰发现被岩石包裹的尚未钙化的恐龙蛋,并成功孵化出恐龙。这一情节被当时的批判者认为是“伪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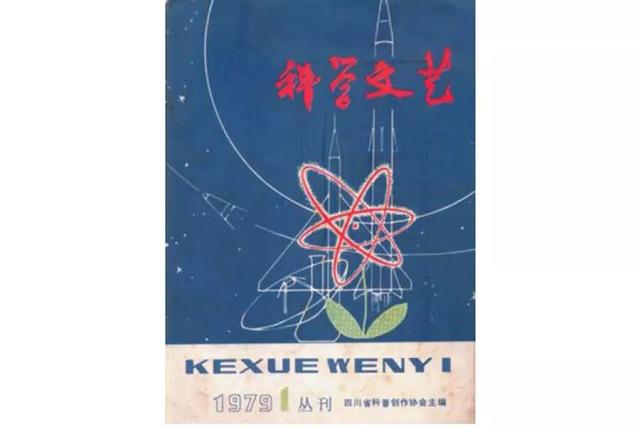
1979年5月《科学文艺》创刊号封面。 (受访者供图/图)
直到1993年,美国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在全球热映;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宣称从河南发现的恐龙蛋中破解了部分遗传密码,人们才意识到叶永烈的想象力有多超前。然而在1980年代初,科幻作家当时的反驳苍白无力。1982年8月,童恩正等十二位科幻作家联名发表公开信,反驳对科幻小说的错误批评。迎接他们的,却是对科幻小说的批判升级。
“搞的风声鹤唳,一片挨打。”《科幻世界》前总编、如今已76岁的谭楷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全国科幻类报刊随即纷纷停刊,到了1986年,《科学文艺》成为中国科幻的唯一火种。
1980年科幻在中国刚刚兴起时,日本科幻作家兼评论家岩上治就创办了日本中国科幻研究会,专门研究中国科幻小说。1986年,岩上治探访《科幻世界》编辑部,他对主编杨潇说:“现在中国科幻刊物都倒了,我们只有研究你们一家了。”
“我们要是停刊了,中国的科幻也就没人搞了。所以咬咬牙坚持了下来。”谭楷回忆当年的孤独与艰难时说,“当时国内要是还有第二家,我们也就不搞了。”
1987年6月,谭楷在《人民日报》发表《“灰姑娘”为何隐退》。文章以“灰姑娘”比喻中国科幻小说,引用爱因斯坦的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呼唤科幻从“某种模式”中解脱出来,卸掉科幻普及具体科学知识的担子。科学家杨振宁看到科幻科普读物在市场上销声匿迹,声援道:“没有哪个科学家是通过看科幻小说来学习科学知识的,但科幻小说可以开拓广阔的思维空间。”
1987年10月、12月,《人民日报》又两次刊文讨论“灰姑娘”为何隐退。1988年2月,在作家马识途的支持下,中国作协四川分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在成都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科幻文学委员会,《科学文艺》主编杨潇等8人被选为委员。
从那时起,杨潇等人开始筹备在中国举办国际科幻会议,为中国科幻正名。
1991年5月,由《科幻世界》主办的世界科幻协会(WSF)1991年年会在成都召开,曾经遭到批评的叶永烈担任大会主席。包括弗雷德里克·波尔、布莱恩·奥尔迪斯在内的亚、美、欧三大洲近两百名科幻界人士出席大会;四川省省长、省委副书记出席了开幕式。亲历开幕式的韩松感到震撼:“巨大的气球,舞狮,龙灯,成都锦江大礼堂中的少儿舞蹈和川剧,无不让人眼花缭乱。”

1991年5月,由《科幻世界》主办的世界科幻协会(WSF)1991年年会在成都召开。 (受访者供图/
重庆科幻作家舒明武曾激动地设想,到了21世纪,成都将成为世界科幻中心,在都江堰建一座多功能大楼,世界各国的科幻作家和科幻迷像朝圣一样来《科幻世界》编辑部。
年会期间,《科幻世界》编辑部还组织中外科幻作家到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与大熊猫合影。韩松对那个场景印象深刻:“熊猫长得白白胖胖,明显得到了关爱,但科幻作家却大多很瘦,有的刚大病新愈,有的坐着轮椅,一副正在‘灭绝’的样子”。
当时参会的还有国家科委科技处处长李小夫。“他来参加会议后深受感动,回去汇报说这帮人是怎么殚精竭虑发展中国科幻的。”杨潇回忆。
1997年,《科幻世界》杂志社主办97北京国际科幻大会,李小夫帮忙联系,成功邀请到美俄两国的五名宇航员参加。参会的俄罗斯宇航员包括别列佐沃依上校,他曾帮助中国培训航天员杨利伟,是当时全世界上太空次数最多的宇航员,因为把大量物资运送到空间站而得到绰号“宇宙搬运工”。会上,第一个在太空行走的俄罗斯空军中将列昂诺夫向杨潇颁发了科罗廖夫勋章,他说,这是此勋章第一次授予一位与宇航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士。
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开幕式发言中再次引用了爱因斯坦的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他说:“如果说,整个世界还徜徉在新世纪的大门之外,与会的各位嘉宾已经比大多数人更早地进入了下一个世纪。”
同样在1997年,中央电视台《12演播室》栏目邀请科幻作家座谈,《焦点访谈》报道科幻。1998年,《科幻世界》首次入选“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社长兼总编杨潇当选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后来又获得了中国出版最高奖韬奋奖。此时,多种科幻刊物在全国各地创刊、复刊,更多的出版社开始涉足科幻出版,中国科幻彻底卸下了历史包袱。
如今,《科幻世界》仍由四川省科协主管、主办。“现在科协的领导对科幻基本形成了共识:科幻不是传播具体的科学知识,而是对创新意识的带动,对科学精神的带动。”《科幻世界》现任主编拉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不会干涉小说创作的自由,我们也不排斥普及具体科学知识的科幻类型,因为它本身是科幻小说一个子类型。”
“中国科幻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我们国家低谷的时候,主流文学还能出很多作品,但是科幻就不行。”科幻作家何夕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次小高潮,‘文革’后‘向科学进军’又有一次,现在是第三次。它和国家的命运好像冥冥之中产生了一些联系,有点儿像一个晴雨表。”
“闯到这个‘贼船’ 下不来了”2019年5月,中国科幻作家何夕、刘慈欣、王晋康、韩松在“另一颗星球科幻大会”上同时亮相。他们被合称为“何慈康松”,听起来像当下偶像男团的名字,不过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已超过225岁。为了见到“何慈康松”合体,许多科幻迷提前两小时在会场门口排队等候。
这四位作家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科幻世界》起步的,如今被科幻迷尊为“四大天王”。四人有次同乘飞机去成都,韩松幽幽地说了一句:“今天这个飞机如果失事的话,中国科幻全军覆没。”

2002年,“何慈康”——何夕、刘慈欣、王晋康(从右至左)在成都听浦江合影。 (受访者供图/图)
早在1979年,中国科幻界曾经流传着老一辈“四大天王”的说法,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刘兴诗是最常见的版本——他们大多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写科幻小说。
1978年,少儿出版社以“在庆祝建国50周年的时候”为题,向叶永烈约稿。叶永烈拿出自己1961年的手稿,改写出版,《小灵通漫游未来》由此诞生。这本书共印了300万册,至今仍然是中国科幻印量最大的图书。
童恩正创作于1960年代的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也于1978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科学文艺》在1979年的创刊号上刊登了由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1980年,同名电影上映。
因为写科幻小说遭受创伤的刘兴诗曾赌咒不再写作,但他还是没忍住,回归了科幻创作。
“文革十年积累了大量的存稿,”谭楷回忆,杂志创刊头两年,他的工作很轻松,“稿子多是比较有名的名家写的,没什么可改的”。
之后,郑文光突发脑溢血从此瘫痪在床,叶永烈改写人物传记,童恩正出国,刘兴诗转做科普工作——曾经的“四大天王”全部隐退。
谭楷统计过,1985年左右,中国作协一千多名会员中科幻作家只有寥寥几个。《科学文艺》从此陷入稿荒,发行量断崖式下跌。
由于科幻稿严重不足,为了填充版面并留住读者,《科学文艺》发表了一批与科学沾边的报告文学作品:《抢救松田宏也》《秦宫一号大墓之谜》《毒酒惨案》《海螺沟,明天的世界旅游热点》……
韩松在翻阅1987年第6期《科学文艺》时发现,当时稿荒仍然严重:“编辑部不得不用非科幻作品凑数,该期共登了三篇纪实报告文学,还有一些历险记、访问记、‘成就动机’随笔、杂记科学散文和科学诗等。科幻小说有8篇,但4篇是微型小说。8篇中仅有2篇是中国人写的……”
1987年,《科幻世界》全体编辑共四人受邀参加日本科幻大会,参观了科幻出版业和青少年科技馆,大开眼界,同时开始接触国际科幻界同行。此后,编辑部组织译者大量翻译引进欧美和日本的优秀科幻小说。
为了开拓国内科幻小说的稿源,编辑部从拮据的经费中拿钱请作者到成都开笔会。韩松由此在1988年第一次探访《科学文艺》编辑部。他印象中编辑部条件很差,“就几张桌子,几个人,没有电脑。编辑部请客吃东西都很节省”。多位科幻作家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科幻世界》也从未拖欠过稿费。
《科幻世界》的主编曾告诉读者:科幻作家都是“生活在光年之外的生物”,要找到他们很不容易。要给他们写信的话,只能由《科幻世界》转达。
1986年,资金紧张的《科幻世界》还创办了中国科幻“银河奖”。他们期待的新一代中国科幻作家,终于次第浮出水面。
1992年,四川大学大三学生何宏伟(笔名何夕)在《科幻世界》发表自己的科幻小说处女作《光恋》,获得银河奖。1997年,何夕忽然归隐,谭楷和阿来去何夕在四川自贡的工作单位。谭楷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我们喝了一晚上酒,拼命煽动他,他又开始写。”
1992年,中年工程师王晋康在儿子的鼓励下,动念发表自己口头创作的科幻故事。他在一个报摊偶然看到《科幻世界》,蹲下来抄了编辑部地址,把自己的科幻处女作《亚当回归》寄了过去。王晋康马上收到了编辑部热情的回信。小说在1993年发表,并获得银河奖。
王晋康原本并没打算继续写科幻。当时他正在做一个大的工程项目,几乎废寝忘食,还评上了劳模。编辑部很快察觉到王晋康不写了,便发来约稿信。“我想,士为知己者死,既然约稿了,再写两篇。”王晋康笑着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几天时间写完了,最后又发表了。从那时候开始,可能正式地闯到这个‘贼船’上下不来了。”
王晋康第一次去《科幻世界》编辑部,在电梯里碰见科协领导。陪在一旁的杨潇和谭楷马上兴奋地介绍王晋康:“这是我们今年新发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作者,他还经常读主流文学呢。”
1995年,王晋康的《生命之歌》发表后,《科幻世界》用整版刊登了读者来信。王晋康读到落泪。“决不是作秀。”王晋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想,图书馆里遮天盖地的都是书,怎么能让读者在这些书里看到你的书,而且喜欢你,甚至成为你终生的粉丝。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的一种恩赐。”
如今,国内发表科幻小说的平台已多了不少,《科幻世界》能给出的稿费只是平均水平,王晋康还是习惯把自己的稿子直接交给《科幻世界》编辑部。刘慈欣、韩松等作家的一些作品则已在其他平台首发。
“我更愿意看到整个中国科幻蓬勃发展。”《科幻世界》副总编姚海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美国有很多科幻杂志,不同风格的作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平台。中国在很长时间内只有《科幻世界》这么一本杂志,要让所有作家都在《科幻世界》有一席之地,杂志本身的风格反而不那么明显,这是历史环境让《科幻世界》不得不肩负的一个使命。现在,不同风格的作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平台。”
环球银幕版的浩瀚星空、科幻天地创刊仅仅两年后,《科学文艺》就曾面临过生存危机。
从1981年起,由于科幻小说遭到批评,《科学文艺》的发行量从22万册最高峰一路下跌,1983年跌至两三万册低谷,主管单位又提出“四自方针”——自寻出路,自主经营,自行组阁,自负盈亏。
1984年,杨潇被编辑部选为《科学文艺》主编,她上任时,杂志社的账上只有6.3万元,发行量两万多册,每年还有几十万亏空。一位好友调侃谭楷,你这样还不如去编地摊小报——当时,东拼西凑、印刷粗糙的地摊刊物很有市场,与《科学文艺》的处境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谭楷只用了一个晚上,就把一些地摊文学作品改名换姓,剪剪贴贴,炮制出一份小报。“头版叫《澡盆里的女尸》,看起来很吓人,配画里一条腿伸出来,”谭楷笑着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其实内容根本不黄,标题党。”最后,这些报样卖了5000元,编辑部每人拿了100元“年终奖”(当时编辑每月工资几十元),其余的钱全部交公。
后来,编辑部填补亏空主要靠制作畅销书,被大家形容为“养鸡喂老虎”。最成功的是少儿科普读物《晚安故事365》,累计卖出七八十万套,每年创下利润几十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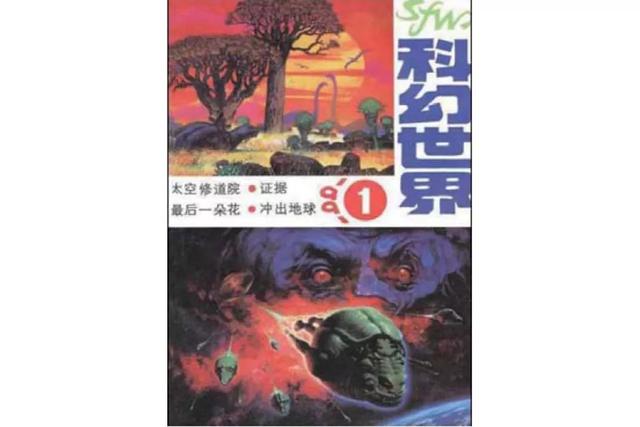
更名于1991年的《科幻世界》的第一期封面。 (受访者供图/图)
卖书养刊的艰难岁月,持续了大约十年。1993年,《科幻世界》将杂志受众锁定为中学生读者,杂志发行量开始大幅上升。1999年,《科幻世界》的产值达到2000万元。《科幻世界》迅速扩张,相继创立了《科幻世界画刊》《惊奇档案》《飞·科幻世界少年版》《科幻世界译文版》等多份衍生杂志。
但自2007年起,《科幻世界》遭遇了第二波生存危机。随着智能手机的诞生与普及,纸质刊物受到巨大冲击,全球期刊发行普遍呈现下滑态势。
早在2003年《科幻世界》杂志社就提前布局图书出版,推出科幻作品丛书。与此前卖书养刊不同,编辑部希望系统出版世界科幻大师的代表作品和中国科幻作家的优秀作品。近年来,《科幻世界》的图书收益迅速增长,2007年出版的《三体》更是跃出科幻圈,成为现象级畅销书。
2009年,《科幻世界》30岁生日,编辑部在第8期和第9期刊发了一套科幻知识考卷,其中一道作文题是:2051年,数字版《科幻世界》由一群顶级程序员负责维护,请用100字以上的文字描述你设计的未来电子杂志的功能、购买方式和防止盗版的措施。
武汉读者熊英畅想,2051年的数字版《科幻世界》将是环球银幕版的浩瀚星空、科幻天地,在这里科幻迷可以与科幻作家影像交流,与其他科幻迷一同玩科幻3D游戏;科幻音乐、电影、图画一网打尽,支持在线下载;盗版杂志则会被种上病毒。
然而,这一天的到来似乎远远早于2051年。2009年就做出预言的《科幻世界》未能赶上这一波潮流的开端。作为拥有中国最丰富的科幻小说版权资源的杂志社,《科幻世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签作品的出版权,而把改编开发权留给作家本人——编辑部曾认为,科幻影视改编的时代还很遥远。
1978年,15岁的刘慈欣写了自己的第一篇科幻小说,投给多家杂志社都被退稿。二十年后,已是工程师的刘慈欣重新提笔完成了长篇小说《超新星纪元》。他留意到两次《科幻世界》主办的年会,并将《超新星纪元》寄给了杨潇。杨潇很快回了一封长信,对刘慈欣赞赏有加,并邀他寄一些适合《科幻世界》发表的短篇小说。1999年,刘慈欣在《科幻世界》发表了处女作《鲸歌》。
1999年底,刘慈欣受邀去成都参加《科幻世界》笔会。那届笔会要求与会者必须带上自己的新作品参加研讨。刘慈欣为此专门创作了《流浪地球》。笔会之后,刘慈欣的短篇科幻小说创作进入了井喷期。2015年,刘慈欣凭借小说《三体》获得雨果奖。
随着科幻重新成为热点,越来越多中国科幻小说的改编版权被买走,其中许多都首发于《科幻世界》。然而,包括《三体》《流浪地球》在内的许多科幻小说的改编权都旁落影视公司。2016年,刘成树担任《科幻世界》社长兼总编,杂志社成立版权部,2019年5月起,刊登在《科幻世界》的新作品,都需要跟杂志社签订版权代理协议。
2019年,电影《流浪地球》上映,《科幻世界》无缘分享影片的巨大收益。编辑部能做的,是用十多天时间赶制了《流浪地球》纪念版图书。导演郭帆为这本书提供了视觉素材,还专门写了推荐语。这本书很快也成了畅销书,至今仍有几大箱《流浪地球》摆在杂志社大厅中央,以便随时发货。
“只要一个民族还能仰望星空, 就还能搞科幻”“几乎每周都有科幻迷来杂志社打卡。”《科幻世界》主编拉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每年9月是高峰期,不少考生因为《科幻世界》而选择成都的高校。科幻迷通常会在杂志社门口与“科幻世界”的招牌留影,然后再找他们喜爱的编辑合影,眉飞色舞地谈论自己熟悉的作品。科幻圈内开始用“幻二代”一词——科幻迷出身的家长会帮孩子订杂志;曾是科幻迷的老师会教孩子怎么读科幻。
科幻迷胥敏如今在成都一所重点中学做语文老师,她要求自己的学生初一读《地球往事》,初二读《黑暗森林》,初三读《死神永生》(注:刘慈欣《三体》三部曲),并写读书笔记。《流浪地球》上映时,胥敏告诉学生,如果观影并写了影评,当次语文作业就评“优”,如果二刷、三刷,评分还会提高。
这样的故事,对于四十年前的中国人来说,本身就很科幻。
科幻迷平台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981年,由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主办、叶永烈主编的内刊《科幻小说创作参考资料》出版,成为当时沟通中国科幻作家和读者的重要刊物。
1988年5月,黑龙江伊春林场工人姚海军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科幻迷协会,会员最初仅有8人,名头却很大,叫“中国科幻爱好者协会”。协会从那时开始发行中国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科幻爱好者刊物《星云》。这是中国科幻界最早的众筹,《星云》的油墨、纸张、邮票,都靠全国科幻迷捐款捐物来支持;“编辑部”开不起稿费,科幻作家和科幻迷就免费赐稿,热烈地发表评论研究、分享科幻信息资料。《星云》就这样办了十几年,姚海军后来进入《科幻世界》杂志社工作,继续在全国发展科幻迷团体。
1992年,《科幻世界》编辑部做了细致的读者调查,发现80%以上的读者是中学生。1993年《科幻世界》改版,开始评选校园科幻作品,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刊登科幻美术和连环画,还连载《林聪讲科幻》,指导青少年写科幻作品。
1994年,三百年一遇的大型彗星将与木星相撞,《科幻世界》组织科幻迷登峨眉山观看。在峨眉金顶,一个学生家长告诉谭楷,她给孩子订了《科幻世界》,她的考虑是:“让娃娃读言情小说,怕他早恋;读武侠小说,怕他打架。儿子既不能早恋,也不能打架,那咋办?读科幻。”
1999年的高考作文“撞题”事件,使得《科幻世界》的订阅数猛增至40万册,这是1991年和1997年两次科幻大会都没有带来的效应。早在1991年,《科幻世界》就在第6期发表过舒明武的记忆移植故事。
高考命题人之一、时任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一处副处长张伟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1999年高考作文题拟为《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是为了解决应试教育造成考生创造性思维范围窄、想象力不够的问题,同时也是适应科教兴国、知识创新的需要。张伟明还介绍,整体来看,作文总体得分比往年要高。
1999年,《科幻世界》主办的银河奖首次将由专家投票改为读者投票。编辑部这样解释这个决定:“我们预料到读者的最终选择将会对我们这些编辑和科幻作家的观念构成巨大冲击,但我们别无选择。因为中国科幻从来不是一种受到特别扶植的事业,她生存与发展的唯一的机会就是读者的支持与理解。”
当时,读者购买的热门外国科幻小说,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作品。这让《科幻世界》的编辑们感到忧心,儒勒·凡尔纳在19世纪的许多幻想早已变成现实,比如环游地球早就不需要80天——凡尔纳已经完全不能代表当代科幻的发展前沿。
1999年,杨潇、谭楷与周孟璞共同主编了《科幻爱好者手册》一书,书中收录了中外科幻名著梗概和最新科幻影视作品概览。2003年,《科幻世界》编辑部启动“视野工程”,为读者系统引进世界科幻大师的经典作品。
《科幻世界》编辑部曾表示:“我们和广大科幻作家,和国内外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一起,聚集在科幻这面大旗下,倡导了一种关注未来的新型文化,倡导了一种富于幻想活力与科学精神的真正属于21世纪的生活方式。”
科幻界有一个“公交车理论”:读者只有到一定年龄才会“上车”,成为科幻迷,过了一定年龄,又会“下车”。1998年,《科幻世界》一次针对3.1万名读者的统计显示,85%的读者是中学生和大学生,他们的平均年龄才18岁。而美国科幻杂志《轨迹》的调查显示,美国科幻读者的平均年龄达到43岁。
拉兹认为,做科幻丛书,可以扩展“公交车”的年龄段。“我们杂志的定位是你大学毕业后就不看了,但我们的书你到三四十岁还能看。”
姚海军记得《科幻世界》发表过一位在美国宇航局(NASA)工作的太阳能专家兼科幻作家的小说《追赶太阳》,讲的是宇航员在月球上陷入困境,为了等待救援队必须追赶阳光,让自己一直处在阳光里以获取能量。小说曾在美国获奖,刊出后,有读者指出主人公绕月球跑一圈的方法比较笨。有科幻迷甚至精确地计算出太阳光覆盖月球的面积和宇航员应该走的路线,意见经《科幻世界》转告作者,NASA和这位科幻作家都大吃一惊,并对中国科幻迷的思考深表敬佩。
更早的1994年,也是三百年一遇的大型彗星将与木星相撞的那晚,谭楷记得那天很冷,他们还租了军大衣御寒。许多人为了用小小的天文望远镜看一眼星空,在峨眉山金顶排起了长队,这让谭楷很感动:“只要一个民族还有好奇心,还能仰望星空,这个民族就有希望,就还能搞科幻。”
(参考资料:《想像力宣言》《追梦人》《穿越2012》;感谢未来事务管理局为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
原地址:https://www.chinesefood8.com/23526.html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下一篇:名字对人生运势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