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人类来说,大灾大疫早非一次了,从未见到病毒把人类消灭。
冰川思享号特约撰稿 | 涂建敏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题记
1月23日,腊月二十九,我们回到江西老家。
传统习惯上,每临年关,日子自然而然切换到农历。这反映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每临年关,一切以“年”为核心。
盼过年的心情不用赘述。准备工作陆陆续续做了半个多月,买了各种伴手礼,老人的、孩子的、亲戚的、同学的、朋友的。又跟单位告了一天假,预计初五返回,二十多年返乡经历,这会是最长的一次。
杭州出发到家全程9小时。没走多远,手机上就传来武汉封城消息。职业直觉,心里隐约感觉不妙,预估形势比预期要严重。
说起来,尽管1月20日那天,钟南山在武汉宣布“无特效药、会人传人”,疫情气氛陡变,但多数人还是如我一般,没能预估到此后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紧张得令人窒息。
01
回家
到家的感觉是温馨的。岳父早已备好充足的鸡鸭鱼羊肉,全部来自家养。
中到大雨,一直下,日夜不停。无法出门,聚餐之余,只能就着火塘烤火,三句话离不开这次疫情。
第二天就是年三十。各种疫情信息不断更新,满屏都是。
雨依旧下个不停。乡村的团圆饭,照例在正午。一大早,岳父母开始筹备午餐。做家务间隙,岳父空然消失了一刻间。雨下得这么大,岳父去了哪里?见我好奇,岳父笑着说:“我刚出去,跟村里几个‘主要的人’打了招呼,今年的请神仪式不搞了!”
主要的人?请神仪式不搞了?!
村里“主要的人”,是个模糊的圈子,大致就是村庄里公认有公信力的人。在村庄,什么是有公信力呢?就是说话做事干脆利索、办事公道、热心公益、为人信服,其中也有村民小组长等,但主要为首的,还是像岳父这样的年尊辈长者。

▲往年热闹的请神仪式(图/作者)
我没追问,这个意见是如何在眨眼间传递下去的,心下倒是佩服起岳父的敏感性来。
岳父不用智能手机,没想到,在我们有一搭没一搭聊天时,岳父就听了进去,而且这么快就行动起来了。
我想,这和岳父的自身经历不无相的。今年67岁的他,15岁上到初一时辍学,16岁开始参与兴修水利,19岁就当了生产队长,带着全村男女老少集体生产。再后来,曾经长期担任社队干部,又搞了二十年农村信贷,至今关心政治。
事实证明,几个“主要的人”行动力是高效的。三言两语,不仅请神仪式说停就停了,就连大年初一互相串门拜年也消失了。
在往年,一大早各家拜年者络绎不绝。三两结伴,成群结对,多数稍作停留,要好的喝上一盅。到了下午,人群散了,长者们便出了门,不乏“主要的人”你来我往,话语还是离不开村庄里的公共事务。
村庄去年重建了祖堂(北方人应该称作“家庙”)。我回来之前两天,刚刚摆了落成酒,来客十二桌,算是告之四方。
老祖堂建于清嘉庆年间,最近一次重修是1949年以后。2006年,搭新农村建设便车,外墙作了一些粉刷,房顶瓦也重整了一下,终归无法摆脱颓败命运,日晒雨淋,摇摇一坠。
在乡村,一座气派的祖堂,既是重要公共设施,更象征着家族荣耀。村庄里没有酒店茶楼,平时有红白喜事,议个事情,祖堂是唯一重要去处。
重修这座祖堂,成了过去十多年焦点议题。每年春节,岳父等几个”主要的人”都要聚在一起议论一番。资金当然是主要问题,当然,也伴随着各房族人之间的分歧和纷争。祖堂重建,折射出这个偏远小山村发展缓慢进程。
现在,就在众所期盼中,总算落成了,全部45万元建设资金,采取丁费摊派加捐资形式。黄坭坵是个自然村,也是单姓村,全村樊姓族人有男丁(包括各家婆娘和媳妇,女儿除外)244人,分作二、四、六、八四房。人均丁费600元,征集144000元,余额则由几个在外经商成功的大户捐齐。
年头到年尾,祖堂最重要的公共活动,还得数年三十年请神仪式。正午开饭前,各家各户用一茶盘,托上三牲供品,聚到一起,由家族长者带头致祭辞,一时间鞭炮齐鸣,硝烟散处,各家各户相互作揖,互致新年。

▲往年热闹的请神仪式(图/作者)
年三十请神,既有请已化作上天之神的先人来尝之意,以表后人感恩,同时也是借此祝福新年风调雨顺。仪式简单而素朴,最早可上溯到明代,几乎没中断过,凝聚着几多家族精神,也使得这个地处湘鄂赣三省接壤之地的偏远小山村祖祖辈辈,绵绵瓜瓞,族聚不散。
照计划,重修落成第一年,这一次的请神之隆重,应为历年之最,而今却因疫情说取消就取消了,怎不让人遗憾。
少了热闹的仪式和活动,村庄显得萧条。
02
小聚
年初一,荣叔从县城打来电话,说无论时局如何,饭还得吃。
荣叔是岳父的大弟弟,近年头一次没有回乡下过年。一来堂舅子勇子在外做水果生意没回来,二来家里孙儿外孙四五个,都扔在县城,根本抽不开。
荣叔上世纪90年代初就去县城做生意,由日用品批发艰难起家,近年又开始经营水果连锁,加盟一家全省果业公司,算是较早成功出走村庄的。

▲乡村花灯(图/作者)
勇子高中毕业后跟着父亲做生意。几年前成了家,荣叔也临近花甲,便逐渐接了班。先是逐渐把零售连锁扩大到了十多家,又在去年上了批发项目。勇子为此新租了店面,购置了冷库设施等,投了四十多万元。
年初二,我和妻子决定去一趟县城,一来透透气,二来探探虚实。天雨一刻不停,呆在屋里,实在气闷得很。
出村庄去县城,走高速40分钟。放在几年前,只能走国道,山路蜿蜒,一路颠簸,要两个多小时。
高速上空空如也,出县城匝道,前面排着两三辆车,逐一测量体温。据说头天开始了这项工作。有交警过来敲敲窗子,示意我们,先把窗子打开,以便于测得准些。等待的瞬间,稍有点儿紧张,所幸车辆不多,量过后放行。
到荣叔家刚坐定,菜就上了桌,菜肴照例丰盛。广东回来的大舅子、在县城工作的小舅子,再就是我们一家。疫情风声鹤唳,年节气不复存在,一餐饭下来,有点心不在焉,一个个心事重重,倒一小杯酒,稍举杯示意,便散了。
全县酒店、宾馆、餐饮、商家一律停业。从荣叔家出来,整个县城一改往日繁华,大街上空旷无人。在小舅子的工作室里坐了会,喝茶,聊天,然后,用过简单的晚餐,仍由高速回了村。
03
噩耗
妻子燕的同学群里,突然传来噩耗,说是一位涂姓同学(不凑巧,刚好与本人同姓),在武汉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了。
“涂学军?”燕有一刻怔住了。回忆好一阵子,想不起有这样一个同学,而且还在武汉工作。也难怪,毕业二十多年,各奔东西,能记得的自然都还记得,不记得的早已遗忘,更何况还是隔壁班呢。
很快地,确切消息传来。说起来,修水是近百万人口的大县,可是,如果从一个县域范围来说,其实还是逃不出熟人圈子。这不,我大姐在家族群中说:“涂的父亲叫涂清波,是你大哥的同学。”
诸多信息汇总起来,终于渐渐弄明白涂去世前大致经历。
农校毕业后,涂一直呆在乡镇,在与湖北交界的水源乡担任镇人大主席。年前不幸查出白血病。去武汉当然是为了治病,修水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几个省会城市里,反倒离武汉更近。可是,就是这一趟治病之旅,直接就送掉了性命。当然,印象中白血病似乎就是不治之症。新冠病毒尚无特效药,免疫力缺损,显然加速了这个死亡进程。
同学们商议如何发起吊唁。一打听,说是人一去世,直接烧了,骨灰寄存在武汉的殡仪馆,老家人不许过去,陪护的家人也被就地隔离。于是,大家各自叹惋一番,说是终归命里有劫数,提议也只好作罢。
事情原本到此结束。可是,很快县内流言四起,先是说水源乡有人确诊了,再后来,又说是武汉治病时染上的,回来后死在家里。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草木皆兵。
好在县里在初五这天发出公告:水源乡公务员涂某因病1月6日去武汉医治,不幸染病于当地去世。探视过的亲朋好友,现都已经过医学观察期。
燕的涂姓同学就这样成了公告里的“涂某”。公告最后强调,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众志成城,共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总算是虚惊一场,
04
回杭
年初三,我们提前中断了这次返乡之旅,早早回杭州。
妻子燕在基层街道工作,年初一单位就开始紧急召集人员上班。疫情走势,也变得更加让人不安,如果一直在村庄呆下去,未来情形会怎样,难以预料。几天来,湖北和武汉人在各地种种遭拒的遭遇,看了让人揪心。
事后看来,这个决定是非常英明的。
年初四,我在厨房做午饭,突然接到岳父打来电话。岳父说,年初三,镇上查到确诊病例。病例发生在集镇中心白马服饰城(说是“城”,其实也就相当于一家普通超市大小)。丈夫在武汉,服饰城则由妻子经营。丈夫年前回集镇过春节,年初一出现发热症状,连着在卫生院挂了几天盐水,然后就确诊了。
突如其来的确诊病例,如同引爆一个炸弹。全县迅速将应急响应由四级升为一级。小舅子后来在电话里说,县长凌晨三点被从床上叫醒,连夜从县城赶到镇上。病人被转运后,卫生院全体医护人员随即隔离医学观察。

▲乡村的田野(图/作者)
县里其后发出公告,公布热线电话,征集去过白马服饰城者的信息,要求密切接触者迅速响应,主动报告,进行隔离。问题是,白马服饰城开在集镇最中心,年头到年尾,有多少人在其中往来进出?这可真是件复杂而棘手的事情。
小舅子接到消息,当即从县城赶回。小舅子在县拆迁公司工作,平时又兼着经营一些宾馆、水果连锁等三产。特殊时局,打破了他的年节计划。在乡下过了除夕后,就回了县城,临走时,把上小学的儿子留在了村庄。
进出集镇的国道被迅速封闭,外来车辆已无法进出。无奈之下,岳父骑一辆摩托,载着小孙儿从村庄一直骑到国道边,小舅子则把车停在国道上等候,“(把孩子)一直送到王屋桥头。”
进出村庄的机耕道被严加把守了。机耕道一头通向集镇,另一头顺村庄通向燕的同学“涂某”工作所在地。再往前就是湖北境内了!这样说起来,惊天骇浪的中心疫区已经近在咫尺。当然,这只是心理距离,实际上,去武汉走高速还得两个多小时。
说到这儿,岳父在电话里连声庆幸:“幸亏你们走得早,否则,就出不来了。”
05
奶奶
岳父送走孙儿,又开始安排起家中事宜。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要保护好家中奶奶。
奶奶出生于1931年,年一过,虚龄迈进九十门槛,她现在是全村目前最高寿的老人了。如果不是这场疫情,家族原定正月初五为她做一场九十大寿,算一算,光至亲就请了八桌。

▲奶奶和二舅(图/作者)
其间,为一位多年不走动的远房亲戚,家人在请和不请间犹豫再三,直拖到年三十才最终定了下来。征求奶奶意见时,奶奶说:“我刚听你们议论好,当即就给亲戚打了电话。可是,想着拖到这么迟才通知人家,又怕人说不尊重,于是自作主张,假称自己老糊涂了,把家里人反复交待的事情给忘了!”
我们听奶奶如此这般复述,都乐了,一边笑一边说:“你看你看,她老人家虽然年岁大,心里头可机灵得很!”赶在年前,岳父又请村里老学究峻峰先生拟了几副对联,其中,还用奶奶名字专门做了嵌名联。岳父说:“至于对联书写,我看也不另请人了,就由几个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来,比比谁写得好,就用谁的。”
忙活半个多月,眼看诸事已定,现在又面临着是否取消的问题。
行事向来果断的岳父,也犹豫起来。我提议,要么再观望观望,等到年初三,看看疫情是否好转。可是,年初一下午,看看势头不对,岳父当机立断,取消寿宴。又和在家的叔叔一道,给亲朋好友们打去电话,一一表达歉意。
爷爷2003年去世后,奶奶仍独居老屋。老屋也是几年前重建的,2009年发了一场大水,全县受灾。后来,岳父向镇上申领了一笔6000元受灾补助,在家几兄弟也凑了点钱,把老屋重建了。
从奶奶后门出去,要经过厨房和猪圈,推开后门,上几个踏步,就是兵叔家。
兵叔是我三叔,他的房子去年刚装修完毕。房子前前后后造了六七年,兵叔和三婶也在外连着打六七年工,一次也没回过家。出门前,先造了屋子框架,等到积攒了足够的资金,终于在去年结束了漫长的打工,把房子装了。
新房煞是气派,上下三层,二楼三个套间。兵叔三婶住一套,空着两套留给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初中辍学后,也在外打工,大儿子成了家,小儿子至今单身,在外做流水线。我想,等到两个儿子能够返乡,兵叔的人生使命,就算彻底完成了。
从兵叔家出去,就是村里茫茫野野的后山。爷爷去世后,就葬在后山上。村里人祖祖辈辈去世,都葬在后山。
村里的青壮年这些年悉数外出打工了,只留下老人。从屋前到屋后的距离,曾经一直是村庄人祖祖辈辈的人生距离。
现在,岳父把奶奶的前门锁了,又叮嘱奶奶说,如果实在憋不住,想出去透透气,就把后门打开,到兵叔屋里转转。说到这,岳父在电话里的语气中满是欣慰。
大概在他看来,做完这一切,奶奶可以做到百毒不侵。
06
宅居
回到杭州,开始宅居。日子过得实在有点浑浑噩噩。第二天起,恢复了中断多时的晨跑。
偌大一个山居楼盘,陷入一片异样安静。市里已经反复号召出门戴口罩。有一两回,偶尔远远看见一两个遛狗的,心下正想着怎样躲避,可是,对方抢先一步,一脚踩到绿化带上,还有一次,对方索性折身走进另一条岔路上。
他是在回避我吗?抑或跟我一样,是出于对对方的尊重?胡乱想到这,先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继续迎头往前跑去。可是,跑出五六米开外,一口气终于没憋牢,瞬间吐了出来,又忍不住,再顺势吸进一口,隐约感觉到对方身体飘过的气息,忍不住涌上一丝担忧,想起加缪在《鼠疫》中的话:
“每个人身上都有鼠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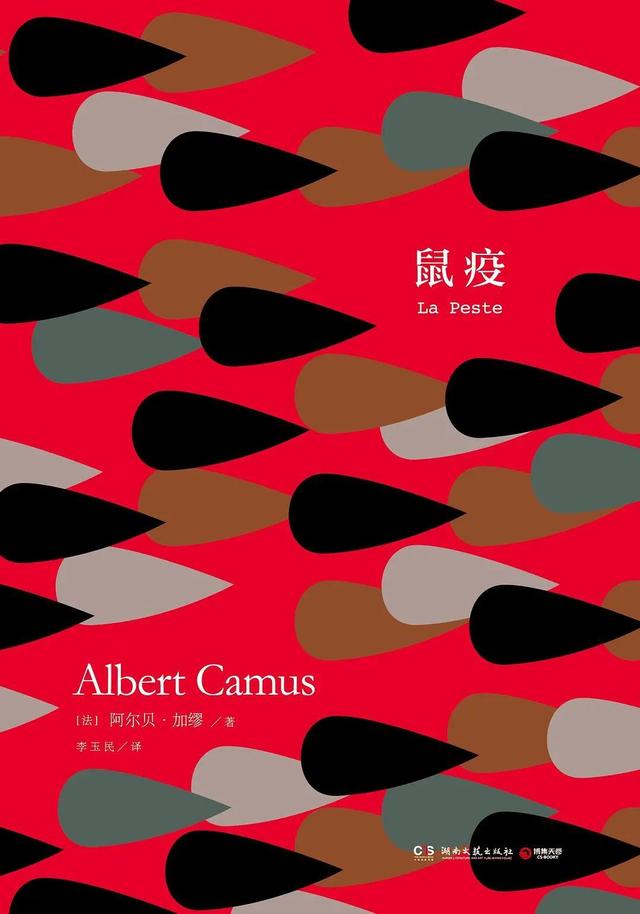
▲《鼠疫》(图/网络)
应该裹足不前,还是就近走走,家族群里也起了争论。
老家大哥在微信群里就抱怨说:“你大嫂胆小如鼠,连我去邻近马家洲公园散散步也严加禁止!”我在群里发言表示声援,“你看你看,小区里连人影都看不到,哪来的传染源!”大哥为有支持者而感到开心,可是,我妈又插话说,“那还是要注意的好!政府都号召过了,少出门,戴口罩!”我侄女也附和说:“确实也是,你如果出去,就必须戴口罩!”争论了几句,没有了下文。
朋友圈里反应各异。
有个搞书法的,年前发了一则朋友圈,大意是小小几个病毒,就把人吓成这样,还配发毛主席诗词《送瘟神》一首,言下之意,以示藐视一切。可我注意到,隔天他就悄然删除了,随后,话风开始变作批评政府。
再过两天,这位朋友就在朋友圈里卖起了书法,只要向红十字会捐款两百元,就能获得他本人书法大作一幅。廉价的书法要同爱心捐赠关联起来,终究要绕好几个弯,但我还是默默祝愿他的书法能够大卖。
此外,在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一位知名诗人发起了“诗歌抗疫”行动,短短几天,据说就已积累了数十首个人诗歌佳作,而且还要火线出版诗集。
我能想象到十万火急之下诗人端坐书房诗情勃发、奋笔疾书的样子,当然,那些隔离在病房内的病人们,恐怕无法读到这些诗歌大作了。那些正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作战在前的一线医护人员,恐怕也无暇拜读这些诗歌了。但是,无论如何,我都祈愿这些诗歌的光亮,能温暖这寒冬里的世间。
还有一位山区的朋友,头天在朋友圈发信息说,“无法讨论国家大事,觉得没有资格。不能感同身受,因为无法体会生死。”
可是第二天,她就在朋友圈里转发一段视频,表示自己彻夜难眠。
视频中,一位武汉女孩追着救护车后头紧跑几步,口中撕心裂肺地呼喊着“妈妈,妈妈……”,可是,追赶终归成为徒劳,在刺耳的警笛声中,救护车拉着遗体呼啸而去,只留下女孩子绝望的喊叫声,划破这个死寂的夜晚。
新闻里报道着各色湖北人和武汉人逃亡的故事。手机里传出视频和文字信息,有武汉人正已经被一轮轮测过体温,可是,仍然没有人肯收留他。
网络上,人们把愤懑之情一次次撒向官员、专家、疾控中心,红会,研究机构。相关官员轮番登场,表示内疚、自责和痛心……
我所在的业主群里,有一天为发现两例确诊病例炸开了锅。
一位母亲,年前就从武汉来女儿处过年,可是,她并没有主动上报,也没有居家隔离,反而四处游走于周边商城、超市等,直到1月30日(正月初六)这天才确诊。也就是说,这么多天,一直活动如初。
消息一经爆出,业主们愤怒地质问说:“为什么之前排查没有发现?”有的很快发来照片,照片中,我住所对面的和轩,正有多名着防护服者全副武装把守。有人希望物管尽快公布这些详细确诊信息,有的则挑剔电梯和公共空间是怎么消毒的。
七嘴八舌间,又有人不知从哪儿当即挖到商城的视频查询记录,并上传到群里。按照记录,这对母女的活动信息,被精确到几点几分,去了哪里,同哪个店员接触过,店员的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一应俱全。
于是,这些详细活动信息,又引发新一轮争执。有人开始对照回忆,同一天是否到过同一家商城。其间也有关心者,向我转发微信,表达关照和提醒。
07
隐喻
连续好多天,醒来第一件事,便是刷疫情数字。此后,不停刷新闻,刷朋友圈,刷各种公告信息,有时候,也会不停转发各种信息,偶尔还配上点评。
我似乎变得有些神经质。我后来想了个办法,从手机设置进去,摸索到各个手机客户端的消息提醒键,把声音一一关了,又把手机放在客厅另一头,尽可能让它离自己远些,再远些。我希望这样一来,至少能够从某种程度上,隔离自己的恐慌、愤懑与焦虑。
我从书柜里找出搁置多年的加缪的《鼠疫》,试图用来努力打发这无聊的寂寞。可是,有时候又不停地从情节中走神。
加缪在《鼠疫》中描述“葬礼”时,如此写道:
“由于棺木渐渐少了,裹尸用的布和公墓中的穴位都不够用了,必须开动脑筋。看来,最简单的办法,而且还是从效率出发,就是埋葬仪式一组一组地进行,必要时救护车在医院和公墓之间多开上几个来回。”
“在公墓的尽头,在一块除了乳香黄连木,其他一无所有的空地上刨了两个大坑,一个埋男尸,一个埋女尸。从这点看来,当局还是尊重礼仪的,只是过了很久以后,迫于形势,方才连这最后一点廉耻之心也丢了:不分男女乱七八糟地往里堆,什么体统也不顾了。”
“救护车运输完毕,担架排成行列抬了过来,让赤裸的、微微弯曲的尸体滑到坑底,大致上还是一具接着一具排整齐。这时先覆盖上一层石灰,然后掩土。泥土只覆盖到一定高度为止,以便留下地方接待“新客”。第二天,家属被叫来在登记册上签字,这标志着人和其他动物,例如狗,这两者是不同的:凭此日后还可核查。”
我无由地想起那位同学“涂某”,当陪护的家人被隔离,遗体烧成骨灰后,至今寄存在当地殡仪馆里,这趟治病之旅,终究成为没有返程的告别之旅。
事实上,《鼠疫》的写作,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1940年代德国对法兰西的入侵,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像老鼠一样”。
加缪在另一篇日记中记下当时的情况:“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抛弃这个背景不谈,现实中的《鼠疫》,何尝不是一则巨大寓言。
春天已经到来,庚子年初的这场疫情,终将会过去。有如我在朋友圈所写:
对于人类来说,大灾大疫早非一次了,从未见到病毒把人类消灭。城市很快就会恢复秩序。人们也终将会是健忘的,就像忘掉2003年那场非典般,忘掉很快成为过去式的这场灾难。除了每个人戴着口罩的样子,终究会像一个烙印,深深烙进每一个人的脑海里。
那会是一个巨大隐喻吗?
原地址:https://www.chinesefood8.com/43533.html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上一篇:腾彩虹月季花黄叶子怎么办?
下一篇:长汀一个女性化的古村落——严婆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