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温州作家哲贵在北京研讨会上。
3月2日下午,北京十月文学院,《十月》杂志为浙江温州籍作家哲贵的小说《仙境》开了一个研讨会,研讨会主题为“地方传统与当代叙事——哲贵《仙境》研讨会”。孟繁华、贺绍俊、梁鸿鹰、张莉、饶翔、岳雯、徐刚、丛治辰等十余位批评家参加讨论。
《仙境》这个短篇小说是近几年《十月》杂志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上过很多文学年度榜。评论家们认为,哲贵的写作从“信河街”以一种悠然简练的调子出发,使用一贯朴素的叙述形式,铺展开每个故事的线条和纹理,在平静的语调中展现、还原出诸多温州当代生活的日常。在小说集《仙境》中,哲贵以一位作家对地方生活形态、行业生态、个人境遇的观察,展现出种种真实人生的镜像。同名小说《仙境》更是将视线由经济生活转移到曲艺领域,以多条叙事线交汇、纠缠出一整部探求精神理想与自我实现的故事。《仙境》跟哲贵过去个人主流的写作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哲贵写商人系列,当然跟传统写商人不是一个路径,他不光是从命运,还有内心的一些东西去挖掘。
《仙境》一开始是一个短篇,最早发表于《十月》2020年第三期,同名小说集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收入其最近四年的短篇作品。一共十篇,最早是2016年的,《归途》比《仙境》早一年写,写作时间最近的就是《仙境》。
哲贵在研讨会上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仙境》对我的写作特别重要,在《仙境》之前,我对世界的理解跟《仙境》之前和之后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角度的不一样。在《仙境》之前,我对小说的理解、对文学的理解,包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都是从外往内看,我是用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的各种力量来压迫小说人物往内心走。但是《仙境》不一样,从《仙境》开始,我对整个世界的理解、对小说的理解、对小说人物的理解做了调整,从内部开始,首先从人开始,从人看历史、看社会、看文化、看经济,所以在《仙境》里面,人物是最主要的,它是摆在首位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仙境》里面人物跟我以前小说的人物不一样,他会更自由一些,也更任性一些。”
“每个作者写作过程中都会碰到“我”,这个写作的人在不在场的问题,在不在场好不好我们不说,因为目前也没有定论,但是在我的写作过程中,特别是《仙境》的写作过程中,也是关系到理解的问题,这个理解跟内外视角的理解,它关系到如何勘探世界边境问题,也关系到世界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如何相对依存的问题,更关系到世界如何建立、塑造和呈现的问题。”哲贵在研讨会上坦言。
那么,《仙境》到底写了什么呢?用评论家徐刚的话来说, “你会发现里面的主人公全都是某一类人,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大老板的儿子或者是接班人,一出场就解决了财富自由问题,家里有矿可以随便造。过去我们谈物质匮乏,今天把物质匮乏解决了,你要面对的就是物质丰腴带来的烦恼。其中有一篇谈到前无光明,后无救兵,谈个体精神高度孤立无缘的状态。所以哲贵的小说要解决什么问题?是有钱之后应该做点什么的问题,这是既具有世俗性,又具有非常普遍的精神意义。”
《十月》主编陈东捷说,“《仙境》离开惯常的题材,他写艺术家的命运,当然中间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比较从容,比较柔软,但也是气韵生动的小说。哲贵整体的写作,过去讲严肃作家,他确实是严肃作家,他对自己要求非常高,不断对自我丰富和突破,哲贵确实是很值得我们将来期待的一个作者,一篇新作出来,我们看完以后大概就会判断他写成什么样,哲贵经常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也突破我们阅读的常规,这样的作家确实值得尊敬,也值得期待。”
陈东捷透露,“有一次我们聊天,他把天下所有写商人的有点名气的著作全部读完,他有一个很宏大的抱负,这个抱负现在还在。”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说,小说的人物是一个商人,同时又是一个隐秘的艺术家,这可能跟哲贵的写作史有关系。哲贵的写作史肯定跟他的现实经验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这又是一个地方传统,可能生在温州的哲贵更能够同时感受到商业文化和浙江文脉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作品不单单是体现了地方传统,它其实是一个当代叙事。戏和商人的关系,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关系。
也有评论家认为,《仙境》的叙事可能是新的中国叙事,就是如何讲述财富,如何去处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他们怎么安顿他们的精神主体。这个故事本身又和浙江温州这个地方牵连着工商业传统,《仙境》特别有意思的是,以信河街为背景,这个背景跟哲贵的非虚构作品《金心》进行互文对读。
以下,是两位嘉宾关于《仙境》的精彩分享——

研讨会现场。
【孟繁华:所有的不可能成就了《仙境》的可能】
孟繁华说《仙境》——
信河街是哲贵的香椿树街或者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在信河街我们可以随处找到所需要的关于哲贵小说创作的消息,或者说信河街就是哲贵小说的后宫,他的好评如潮的短篇小说还是来自信河街,他取名《仙境》,与其说《仙境》讲述一个故事,不如说它讲述一个神话,在现实或者逻辑的意义上,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故事。故事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悖论,或者说是一个不可解的悖论,这个悖论就是鱼和熊掌的悖论。子承父业,做一个皮鞋帝国的王者,是余展飞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生前景。事实上他也确实接过父亲皮鞋帝国的王位,在当下价值观中,这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人生。但余展飞心有不甘,他看过舒晓夏的越剧《盗仙草》之后执意要学习,学习的动力来自越剧演员舒晓夏,余展飞看过舒晓夏扮演的白素贞之后改变了人生,他原来的人生除了皮鞋还是皮鞋,是她演的白素贞让他看到除了皮鞋,他的生活还有梦想,而且是一个只有他看得见、摸得着的梦想,或者换句话说,她演的白素贞让他突然从眼前生活中飞出来,让他看到原来没有看到的东西,那些东西是他以前没有想过的。于是余展飞便和越剧团的前辈俞小茹学戏,余展飞确实是一个学戏的材料,他学演白素贞能够让越剧团台柱子舒晓夏感到巨大的威胁。这个威胁对舒晓夏来说并不陌生,她曾经给过俞老师这种威胁,当她第一次正式登上舞台成为白素贞后,她从俞老师的眼神看出来她是多么哀伤,多么无奈,那是走投无路的绝望,这种感觉不是长驱直入的,而是馄饨的、弥漫的,是眼睁睁看着自己枯萎的悲凉,眼睁睁看着自己消亡却无能为力。
梨园行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它和学界不一样,学界抓住一个好学子喜出望外,巴不得你的文章比我好。但是演戏真是不一样,为什么有的老师要留一手?就怕你超过他。包括武行也是。
舒晓夏的感受,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余展飞在学习方面的精进,余展飞天才的演戏能力使他有机会进入越剧团做一个专业演员,当这一切都有可能的时候,余展飞拒绝了,余展飞还是子承父业继承皮鞋帝国,但是余展飞的梦想还在《盗仙草》中展翅翱翔,一上台余展飞就忘了音乐,他不需要音乐,他要的是仙草,音乐变成一种提醒,让他不断向前,不断飞翔的提醒,回到台下余展飞依然沉浸在那种情绪和情节中,白素贞口弦仙草飞向许仙,她似乎听见舞台下巨大的掌声,看到俞老师跑到后台,激动的抱住他,不停的跺脚。这个写得太精彩了,这一个跺脚动作把一个人一览无余呈现出来,这是哲贵的高明。
据哲贵说,这个小说是源于一个鼓词艺人办起服装公司,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在上海挂牌上市,成为全国很有特点的服装企业,除了做服装特别注重文化建设,建立中国第一所服饰文化博物馆,请专家编撰服饰书籍,他每次出现在公共场合,眼镜一次一换,头发丝毫不乱,有人说他身上穿的都是自己设计和定制的,看不出和其他企业家有什么不同,这估计是有意为之的,他每次强调穿的是公司生产的牌子,再平凡不过。有人也注意过,他发言讲到忘情处会翘起兰花指,脸色绯红,连声调也变了,可仔细一听又没有变,他是受人尊敬的企业家。很多时候大家忘记他曾经是鼓词艺人,可是在儿子结婚典礼上,他突然搬出鼓词乐器上台唱了十四娘收妖。
这个鼓词艺人的经历平平常常,没有特别之处,但是鼓词艺人的所作所为都是正常的、可能的,而《仙境》确实是由一系列不可能构成的,如前所述,大结构是鱼和熊掌兼得的结构,余展飞既继承父亲的产业,同时也实现他在舞台上名副其实的白素贞。在一系列细节上是不可能推动小说的发展,舒晓夏将排练场所挪到宿舍是为了以身相许,但余展飞拒绝了舒晓夏的申请,虽然后来舒晓夏说余展飞爱的是白素贞,并不爱现实的舒晓夏,但现场余展飞没有确实拒绝舒晓夏的理由。你虽然当过和尚,当你还俗之后,你有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余展飞成为33亿富豪向舒晓夏求婚的时候,舒晓夏拒绝了。这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能的,一个女孩子嫁33亿的富豪,那个富豪除了有不可接受的理由,他是不可能去拒绝的。按照现在的价值观,舒晓夏过于书生气的理由没有说服力,更何况舒晓夏那么喜欢余展飞,余展飞父亲突然去世,舒晓夏不同意嫁给余展飞,却同意在余展飞父亲葬礼上出演白素贞,最后舞台上出现舒晓夏和余展飞两个白素贞,现实中也是不可能的,一个戏里面出两个白素贞算怎么回事?有趣的是正式这些不可能成就了《仙境》的可能。
李敬泽有一次讲,小说是写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对的。不可能的是小说,可能的是报告文学,这就是虚构和非虚构的重要差别。非虚构一定是可能的,虚构一定是不可能的。《仙境》是一段时间以来特别优秀的小说,写得结实、感人,在小说内部几乎很难找出可以诟病的漏洞,但是读过之后我还是难以释然。一方面信河街的富人们无所不能的既拥有价值33亿的资本帝国,同时也拥有可以任意飞翔的艺术之梦,如果这还不是仙境,什么是仙境?或者这个世界就是为能够进入仙境的富人们准备的。哲贵这些年来执意书写信河街的商人群体,这是他对书写对象选择的自由。但是对信河街富人无所不能,甚至可以自由进入仙境的神功伟力,这究竟是炫耀?还是示威?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在文学意义上他们是平等的,作家都可以书写。但是如果略去富人拥有巨大资本的前史,仅仅肆意放大他们今天的从容、执着、追逐做梦,这真实吗?
另一方面,《仙境》并没有凸显金钱的价值,特别是舒晓夏,并不是因为余展飞有33亿就恨不得早早委身于他。她在排练的时候试图一身相须,因为她真实喜欢余展飞,当她发现余展飞喜欢舞台白素贞的时候,断然拒绝余展飞的求婚甚至对排练场的投资。对于余展飞来说,家庭的富裕和后来的富有,金钱使他获得自由,他可以造皮鞋,也可以演《盗仙草》,金钱并没有使他肤浅和庸俗,如果这样,这有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矛盾,我这个困惑不管是不是有意思,我都不能否认《仙境》在当下语境中确实是一部特别好的小说。
还有一点,哲贵这个宏大的抱负,起码在小说创作领域里面独具一格,我就是要写富人。你们写穷人,写打工族、底层写作,我不是,我写富人阶层。富人阶层也是人,执着的去这样一个阶层在今天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他们的精神和思想状态,我觉得特别需要。至于写没写他的前史,你如果没写,可能有人还会写。现在写富人绝对政治正确,特别是受到底层人普遍的欢迎,但是这里确实有民粹主义思想,如果我们完全支持这种民粹主义思想,我们的文学创作可能是有问题的。

评论家们:左二,孟繁华。三四张莉。
【张莉:他不会按社会学的思路去处理他的商人】
张莉说《仙境》——
《仙境》我去年的时候年选选过,哲贵的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里也是独树一帜的,这个独树一帜首先是信河街已经构成它的文学原乡,这个文学原乡在最初刚认识哲贵的时候是一个雏形,但现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饱满,先前也跟哲贵讨论他里面提到的那些人物有可能有一些单薄或者有一些我们进不去的,孟老刚才也提到那些富人们的生活不是特别能够引起共情,但是这个《仙境》,我去年就跟哲贵说,我特别喜欢《仙境》,它非常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人的复杂性,已经让我们忘记他是一个有钱人或者没钱人。很重要的是他是怎么构建人的复杂性,我的发言标题叫“通灵的手艺人”,这个小说里面的余展飞有自己暗示的人,女性文学里面有“一个人的房间”,对于《仙境》里面的余展飞来讲,他有自己的房间,就是那个戏台。那个戏台承载了他作为一个个人的、非公共空间里面人物形象的部分。所以不论是《盗仙草》还是白素贞这个形象,一方面他热爱艺术,在白素贞身上有他对整个世界的理解,另外一方面,在白素贞身上也有他难以为别人所理解或者所认知的暧昧的性格那一面,他把这个性格比赋到白素贞身上,所以他为什么看到白素贞特别渴望成为她,渴望在舞台上演绎,从我的角度来讲,他势必有在现实生活中无法传达的内容借助人物去表达,因为这个人物不仅仅在皮鞋厂工作,不仅仅是一个家业,不仅仅是赚钱,还有那个妖娆的、传奇性的白素贞的一面,所以这个人物气语鲜活生动,所以这是认识余展飞的一个抓手,进入他之后就进入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人的空间。
进入余展飞这个人物的时候,他构建的时候有两个线,一个是他和《盗仙草》、皮鞋厂之间的选择,第二个是他和舒晓夏之间的关系,如果用心理分析的角度讲就太多了,他使不可能成为可能,两个白素贞在舞台上,一个白素贞是非常英气的,另外一个是哀伤的、凄婉的,我们原本以为哀伤的、凄婉的是舒晓夏,那个雄健的我们原本以为是余展飞,但是恰恰他们两个做了性别的置换,哀婉的是余展飞,另一个是舒晓夏,这两个白素贞,从表面上来讲代表我们今天对白素贞的两种理解,两种理解都是对的,当然也可以合二为一,但是这两个人物他给分成两个部分,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实际上余展飞和舒晓夏是两个自我。
看《仙境》的时候势必会讨论到他前面有一个中篇小说《青衣》,《青衣》写嫦娥奔月,一个女性饰演嫦娥中遭遇的困境,那里面也写两个自我,一个人的分裂,一个中年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在不断的日常磨损里面已经没有那个仙气,但是你在舞台上特别渴望获得她,所以人的自我割裂,在这个自我割裂里面有一个年轻的角儿和老的角儿之间的争斗,筱燕秋和他的师傅、和他的徒弟的争斗,《仙境》里面也讲到一种争斗,但这个争斗变成一个男和一个女,这个男和女之间关系发生变化,他们两个有床上戏,这个男人跟她讲不能,从我作为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他们俩永远不可能结婚了。他们两个有钱了,他愿意跟那个女人结婚,舒晓夏已经成团长,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很明显的,他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幸福都没有,为什么要跟他?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他写了非常隐秘的人性的幽微的部分。
我们看到的信河街商人就是这样,他所向披靡,他有钱,也没有什么性格缺点。但是余展飞这个人有很大的心,在外人看来他有性格缺陷,但是皮鞋厂让他看起来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成为一个愿意在日常生活中活着的人,但是《盗仙草》和白素贞有他非生的一面。我觉得好的小说其实是写出一个人的两面性,一个人有他的社会性,他在社会环境里所说的、所想的、所表达的,但那恰恰不是他想做的,那些所谓见不得人的、被人看不见的,他自己其实是觉得舒服的,而哲贵用白素贞和《盗仙草》的方式,尤其是《盗仙草》这个名字也讲得很好,当然它是一出戏的名字,当他盗仙草的时候,一个人内心的渴望,如何把外在自我和内在自我进行结合,如果这个人皮鞋厂也很成功,在塑造白素贞的时候又能够真正感受到那种换角色的幸福,那可真的是精神上的仙境。但他是不是真的找到了?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发现也未必,他有内心的巨大遗憾,即使他什么都有了,但是依然得不到另外一个白素贞,而且那个白素贞永远不可能嫁给他,因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嫁给同一个自我。到了形而上层面的时候,这个小说就特别有意思了。以前做女性文学研究有一个观点,我在性别观调查的时候也问过很多作家,就是你是否同意好的小说家雌雄同体。很多作家的回答,理想状态肯定是雌雄同体,但是你要跨越自己的性别达到雌雄同体很难。
我觉得《仙境》倒不是说小说家想跨越,而是这个人物一直内在渴望跨越一个障碍,然后达到他自身的雌雄同体,达到他的平衡。但是他是否做到?小说后边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能够感受到一个人通灵以后,我为什么说主题是“通灵的手艺人”,手艺人是说他是皮鞋厂老板,《盗仙草》和白素贞是他通灵的方式,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既表现作为余展飞这样的富人阶层内在精神上的某种困境或者某种可能都可以,但另外一方面,他的确也书写了这个阶层特别的地方,一个皮鞋厂的老板做鞋做得好,有几十亿,其实并不是让人觉得特别有趣的事,但是他在他父亲的灵堂上出殡的时候唱一出《盗仙草》,这个人就有意思了,就是因为这个复杂性、多面性和双面性,这构成《仙境》吸引人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讲,哲贵以他的这个短篇显示他对人的理解的复杂性和对富人理解的复杂性。我们为什么觉得哲贵以前写的富人哪里缺了什么,但是《仙境》让我们看到哲贵某种程度也盗到他的仙草。当然它的前世部分,对于余展飞来讲可能是他的父亲,再往前推,可能我们想看到历史的深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重点不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历史深处,但是让我们看到他的灵魂和心灵、对自我认识的深处,这种对自我认知的深度在当代小说创作里还是拓展了一个方向。
我们通过哲贵的小说已经非常熟悉在温州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商业上非常有名的街——信河街,他熟悉信河街,熟悉信河街的商人,他也熟悉这些商业活动。它跟我们读到的那些写商人的小说的确非常不同,而且大家都在讨论哲贵写商人从来不按大家的那种思路写无商不奸,不从大家普遍接受的思路去写商人,当然首先有一个情感原因,他熟悉他身边的朋友经商,他并不一定要站在共同的道德立场上对他们的商业活动进行批判,有这种情感原因。但我觉得更主要还不是情感原因,他了解他们,他从他们身上找到另外一种进入文学的路径,哲贵要超越我们比较熟悉的而且公共化的二元对立的思路,财富和道德是对立的,物质和精神是对立的,世俗和理想是对立的,对于哲贵来说,他想找到另外一个进入文学的路径,而不是从二元对立的路径去处理他的那些材料。他找到另外一个路径,所以我们读他的小说,可能社会学层面的东西被淡化了,他会写到商人,会写到商业活动,但是他不会按社会学的思路去处理他的商人。所以阶层这样的思路不能很好的解读哲贵的小说,比如《仙境》里面的制鞋老板30亿的身价,你完全可以说他是资本家,他是富人阶层,但是用这样的思路去解读小说不是很妥当。他更多的是想进入人性的层面,他有他的重点目标,对于哲贵来说内心更向往自我,向往精神自由,他更看重个性,看重艺术,看重美,在他的心目中,他去写商人,他更愿意写商人的自我怎么实现的,他们的那种精神自由是在商业活动中怎么处理的,他是从这个层面进入商人。所以他写商人跟我们文学构成的谱系不是太搭界,他不是从道德层面对商业这样的社会活动进行思考,所以我是这么理解哲贵的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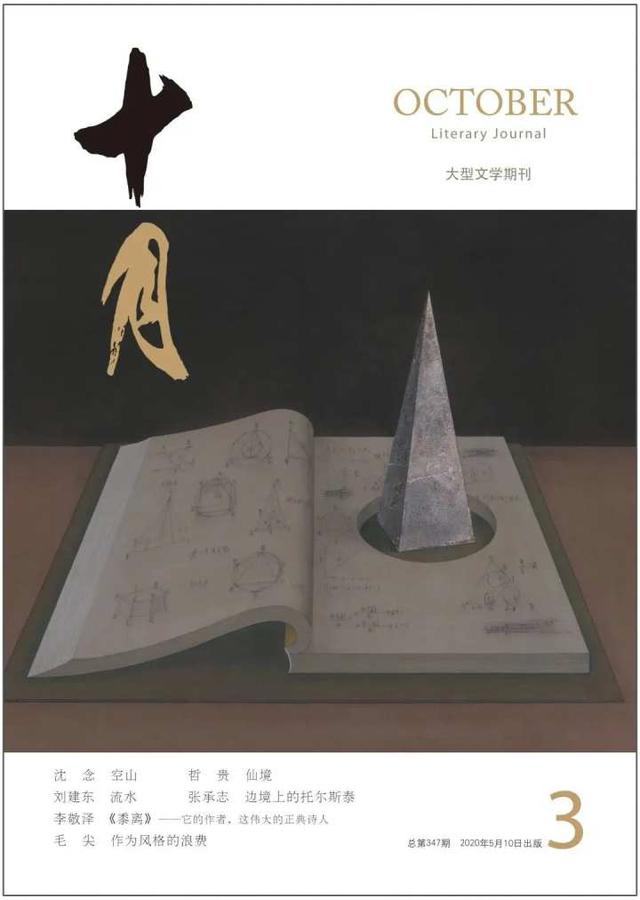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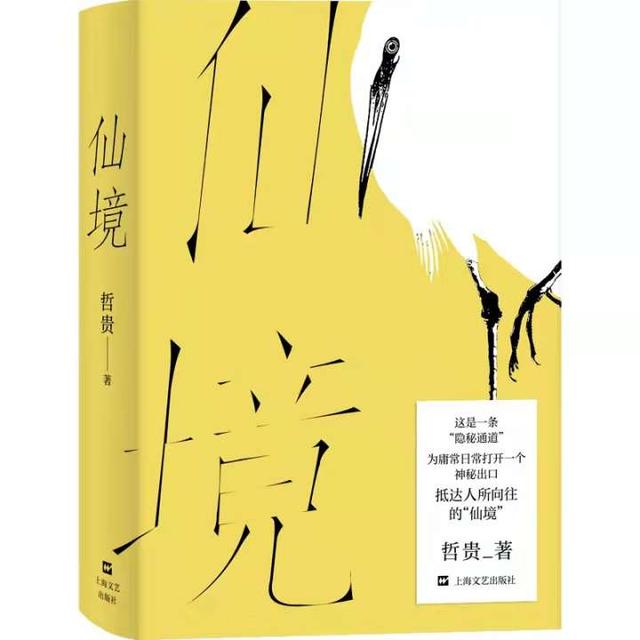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原地址:https://www.chinesefood8.com/45000.html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