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戈铁马的十六国,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让人感到混乱、陌生又不乏一丝神秘感的时代。“三分归一统”的西晋王朝匆匆收场,北方历史舞台上突然出现了一大批匈奴、羯胡、鲜卑、氐、羌等势力,虽然他们大多已经在华北、关中定居了几代人,但直到这时史书记载的聚光灯才照向了他们。在十六国的英雄榜上,石勒无疑是居于前列的人物,这位山西武乡长大的羯胡所经历的起伏坎坷,可以带我们领略彼时从最底层到最高层的全幅风景。新整理点校的《十六国春秋辑补》(北魏崔鸿撰,清汤球辑补,聂溦萌、罗新、华喆点校,中华书局,2020年)将石赵相关的史料集中到短短数卷之中,为读者省下许多搜集之苦,我们正可借此走近石勒和他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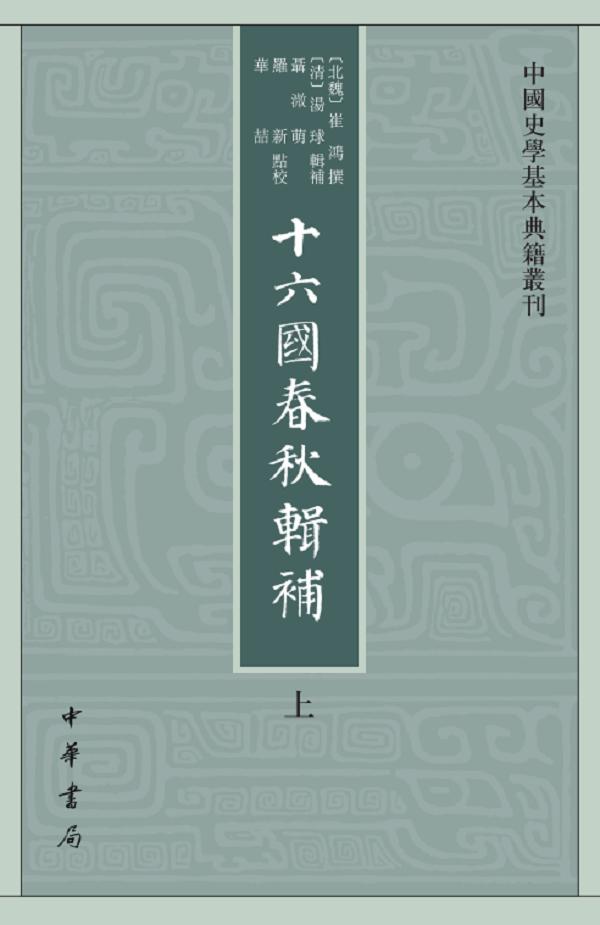
《十六国春秋辑补》
一、卑辞擒王浚
公元313年,石勒第三次攻下邺城,司州、兖州、冀州大片地区已尽在掌握,成为北方一大势力。此时晋朝留在北方的残余力量还剩下并州的刘琨与幽州的王浚,他们分别依靠拓跋鲜卑和段部鲜卑的援助,与刘聪、石勒形成对峙。对于在河北发展的石勒来说,幽州的王浚是当下最大的威胁。王浚“据幽都骁悍之国,跨全燕突骑之乡”(石勒语,以下未扩注出处的引文均来自《晋书·石勒载记》与《十六国春秋辑补·后赵录》),署置百官,称制南面,已经着手代晋称帝,孰料翌年的三月三日,却在大本营蓟城被石勒兵不血刃地活捉了。此中曲折,颇可玩味。
在对王浚动手之前,石勒听从了谋主张宾的建议,“夫立大事者,必先为之卑”,派遣两位使节带着大量珍宝和一封劝进王浚为天子的表文前往幽州。表中写道:
勒本小胡,出于戎裔,值晋纲弛御,海内饥乱,流离屯厄,窜命冀州,共相帅合,以救性命。今晋祚沦夷,远播吴会,中原无主,苍生无系。伏惟明公殿下,州乡贵望,四海所宗,为帝王者,非公复谁?勒所以捐躯命、兴义兵诛暴乱者,正为明公驱除尔。伏愿殿下应天顺时,践登皇阼。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当察勒微心,慈眄如子也。
石勒为上党郡武乡县人,属于并州,而王浚出身太原王氏,为魏晋时期第一流高门,当然也是并州首望,“州乡贵望,四海所宗”一语,可谓正中其怀。更有说服力的是“勒本小胡,出于戎裔”,在当时的语境下,这是近乎自辱的卑辞。王浚仍然质问其使者王子春,石勒已拥有强大实力,为何称藩,可信吗?王子春回答:
石将军英才俊拔,士马雄盛,实如圣旨。仰惟明公州乡贵望,累叶重光,出镇藩岳,威声播于八表,固以胡越钦风,戎夷歌德,岂唯区区小府而敢不敛袵神阙者乎。昔陈婴岂其鄙王而不王,韩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争故也。石将军之拟明公,犹阴精之比太阳,江河之比洪海尔。项籍、子阳覆车不远,是石将军之明鉴,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之所许耳。愿公勿疑。
除了重申“州乡贵望”,王子春着重发挥的是“帝王不可以智力争”的论点。举陈婴、韩信等例,明显有两汉之际班彪所撰《王命论》的影子。帝王之位因天命而非逐鹿获得,而天命在于刘氏,这是西汉后期尤其东汉一朝力图灌输的思想,其影响非常深远(参看侯旭东《逐鹿或天命:汉人眼中的秦亡汉兴》,《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但正如曹丕在禅代仪式中说出的“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枭雄无不知晓,只要军事政治实力具备,天命、符瑞、民意都是可以制造的。真正打动王浚的,还是那句“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之所许耳。”和天命说相比,华夷秩序的观念发轫于战国,完备于两汉,甚至是比天命论更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其核心要点是华夏居中统治四夷,四夷居外接受统治,天命或许会转移,但绝不会从华夏转到夷狄。夷狄要想做天子,不仅上天不同意,人民也不允许。王浚之流对此毫不怀疑。两年之前,刘琨曾送石勒之母王氏于勒,同时也带了一封诚意满满的书信,其中写道:“自古以来,诚无戎狄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石勒并未正面反驳,只是回复道:“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王子春的说法与刘琨的书信如出一辙,说明这是当时颇为流行的“常识”,它能让石勒无法反驳,也能使王浚打消疑虑。这就是王浚接受石勒“称藩”的心理基础,此后石勒向王浚使者示弱的表演才得以展开。在下一年三月三日(上巳节),石勒带着大军,赶着数千头牛羊奔向蓟城,王浚坚信石勒是来称藩奉戴自己称帝的,在沿途准备好食物接待。等到数千头牛羊填塞街巷,让幽州士兵无法出动,石勒便长驱直入其府中,王浚毫无反抗地成了阶下囚。
二、“小胡”印记
石勒的谋略能够成功,固然是由于王浚华夷观念根深蒂固,也因为石勒的“小胡”身份的确明显。石勒是“羯胡”,据唐长孺先生考证,羯胡应是较晚徙入山西、河北地区的塞外北族,他们在草原上曾是匈奴的属部,因此也被目为“匈奴”,但在自居匈奴正统的“五部”看来,他们只不过是来历不明的“杂胡”。羯胡中含有相当多西域来源的人群,但他们并非直接来自西域,而是首先成为匈奴属部,再从北方草原进入汉晋边塞之内的(唐长孺《魏晋杂胡考》,收入《唐长孺文集·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石勒一家就属于这类具有西域、匈奴双重渊源的人群。史言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羌渠是一个常见的名号,东汉灵帝的南匈奴有位单于名羌渠,而在此之前已经出现过乌桓大人羌渠,所以石勒的先世未必就是魏晋时期入塞匈奴十九种的“羌渠种”(《晋书·北狄传》)。在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中,有一条辑自《太平御览》而不见于《晋书·载记》的材料:
张季字文伯,羌渠部人也。颇晓相法,常谓虎曰:“明公之相,非人臣之骨。”虎掩其口曰:“君勿妄言,族吾父子。”
这里的羌渠部人张季,姓、名、字俱全,且精通“相法”,其华夏化的程度已经不低。再看石勒,其祖名耶弈于,父名周曷朱,又名乞翼加,都是典型的胡族名号,没有华夏式的姓名。石勒家族大概率不属于张季所在的羌渠部。石勒的胡名为㔨,“石勒”,是他跟随汲桑起兵之后,后者为他取的汉字姓名,那时他已经32岁了。“㔨”这个罕见的字,数次出现在与石勒相关的人中,很可能是专门用来对译某个羯胡语词。也许它与北族中普遍存在的统率名号Bäg同源,该词在中古北族的名号中常对译为汉字“跋、弗、伏、匐、发、伐”等(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收入《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些都是入声字,而与背同音的㔨则是一个去声字,对译汉字的不同大概反映了羯语与鲜卑及突厥系语言的区别。用这个字取名的还有石虎的祖父“㔨邪”,他应是石勒的叔父。另外,石勒早年随汲桑起事失败之后逃回山西,前往投奔一位壁于上党的胡部大张㔨督,三言两语陈说利害,就让张㔨督跟着自己去投奔了刘渊。夺取㔨督数千部众的指挥权后,石勒命㔨督为兄,赐姓石氏,赐名曰会。同样的人名意味着相似的语言,同为上党杂胡又多了一份地域认同,再加上同为匈奴属部的身份和对单于号召力的承认,正是利用了这些背景,石勒才能说动张㔨督,他们才会结为兄弟。石会后来成为石勒手下的将领,在攻占匈奴汉国首都平阳之后,曾“奉命修复元海、聪二墓,收刘粲已下百余尸葬之”,完成了一个匈奴属部杂胡对单于的最后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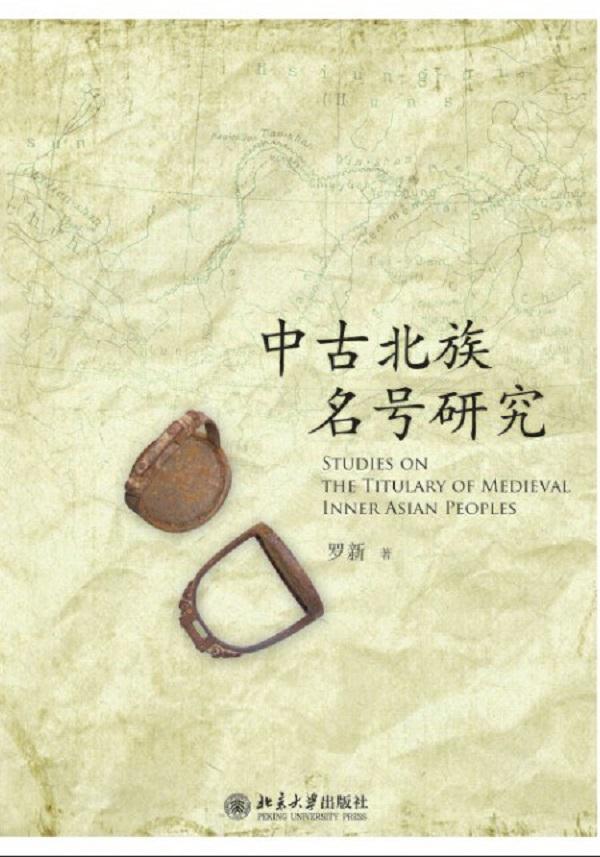
《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石勒不识字,但一定会说汉语(当时称“夏言”、“晋言”),而羯胡也有自己的语言,他至少熟练掌握两种语言。石勒称赵王时,曾发生过这样的事:
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讳胡尤峻。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勒大怒,谓宫门小执法冯翥曰:“夫人君为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宫阙之间乎。向驰马入门为是何人,而不弹白邪?”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驰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
冯翥说胡人“不可与语”,其实是说他们之间语言不通,石勒心领神会,又引申为“胡人正是不那么好说话”,表达了对赵国内部胡人获得特权地位的欣慰。羯胡的语言,来自西域的高僧佛图澄也懂得,在石勒与刘曜决战前夕,石勒向佛图澄请教吉凶:
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
这十个字曾引来众多历史语言学家的兴趣,试图从中还原出一种可以辨识其系属的古代语言。我不敢说这种语言属于突厥语族还是伊朗语族,但至少不能直接用它来研究匈奴语,因为羯语不能等同于匈奴语。如果石勒也能说匈奴语的话,他应该掌握三种语言了。高欢可以同时用鲜卑语和汉语发号施令,还能欣赏斛律金用敕勒语唱的歌曲,安禄山“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处在文化边缘地带的人们往往具备多语能力,古今莫不如此。
石勒身上的“小胡”印记,还有很多。比如他母亲王氏,单看姓氏未必是胡人,但她去世后被“潜窆山谷,莫详其所”,而后又虚葬于襄国城南。石勒本人死时,也是“夜瘗山谷,莫知其所,备文物虚葬”。石勒称赵王时,曾“禁国人不听报嫂及在丧婚娶,其烧葬令如本俗。”所谓“报嫂”,就是“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史记·匈奴列传》),研究者称之为“收继婚”,这是匈奴中盛行的习俗。而“烧葬”则不行用于匈奴,匈奴墓葬迄今已发现数千座,虽在墓葬规格和形制上具有多样性,但绝大多数墓中都有仰身直支的墓主人骨骼,与火葬后以骨灰入葬迥然不同(单月英《匈奴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火葬习俗流行于西域,粟特、焉耆等都奉行此法,羯人的烧葬或与其来自西域有关,上述潜窆虚葬的做法很可能是与火葬配合进行的。石赵的宫殿中有“胡天”,一般认为是祆教的祠庙,如果羯胡像粟特一样信仰祆教的话,火葬便更加自然了。由此看来,石勒母亲即使不是羯胡,也已经羯胡化了。羯胡“本俗”中的收继婚与匈奴相同,又有不同于匈奴的烧葬,再次显示了其双重渊源。不过,在石赵统治期石氏家族的葬俗可能发生了变化,《晋书·慕容儁载记》写道:
儁夜梦石季龙啮其臂,寤而恶之,命发其墓,剖棺出尸,蹋而骂之曰:“死胡安敢梦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阳约数其残酷之罪,鞭之,弃于漳水。
石虎的墓葬不仅轻易就被发现,从中还挖掘出了他的尸体,充分说明石虎死后没有采用烧葬、潜窆、虚葬的做法。此中原因,或许是石赵建国后接受了更多汉晋华夏文化吧。
石勒等羯胡的长相也具有西域特征,即高鼻深目。在石赵后期曾发生这样一件事:
太子詹事孙珍问侍中崔约曰:“吾患目疾,何方疗之?”约素狎珍,戏之曰:“溺中则愈。”珍曰:“目何可溺?”约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诸子中最胡状,目深,闻之大怒,诛约父子。
孙珍眼窝深,崔约就和他开玩笑说往里面撒尿能治疗目疾,没想到触怒了同样目深的太子石宣,招来灭门之祸。孙珍和石宣“胡状”的表现是目深,这反映了时人对“胡”的印象。中原的华夏人用“胡”来指称的对象,在战国和西汉主要是北方的匈奴与东胡,而到东汉以后,“胡”的含义中用来指西域背景的“西胡”的成分越来越重。北亚的匈奴人、鲜卑人并不天生高鼻深目,汉代文字史料中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相貌几乎没有记录,但在图像资料中,比如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那个匈奴人就长着一张扁平的大脸。东汉画像石等图像中高鼻深目的胡人明显多了起来,研究者认为这与画像的“格套”化有关,也就是说并不一定写实。(邢义田:《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收入《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不过西域胡人的高鼻深目确实存在,也确为汉人所知,《汉书·西域传上》写道:“自宛以西至安息国,……其人皆深目,多须髯。”这句话来自汉朝派往西域使节的报告,新疆出土的众多“干尸”也映证了这一点。“匈奴”是一个复杂的政治体,在其统治下不乏来自月氏和西域诸国的人群,这些容貌特异的胡人更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久之“高鼻深目”就成了中原人对胡人的刻板印象。就像上世纪国门未大开之前,中国人常以“金发碧眼”去概括欧美人的长相,可真实的情况是,金发碧眼者(blond)只是欧美人中很小一部分。回到上举石宣的例子,其母姓杜氏,大概率不是胡人,他的相貌特征只能遗传自其父石虎。由此推断,石勒家族在长相上应该符合人们心目中的“胡人”特征。石勒本人的长相很有辨识度,少年时家乡父老就说他“状貌奇异”,后来被卖到河北平原的茌平县为奴时,其主人师懽“奇其状貌而免之”。“胡状”辅助了石勒的创业,也见证了后赵的覆灭:
季龙造太武殿初成,图画自古贤圣、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皆变为胡状,旬余,头悉缩入肩中,惟冠䯰髣髴微出,季龙大恶之,秘而不言也。
这里说“变为胡状”,说明这些壁画上的贤圣、忠臣、孝子、贞女,原本应是前代华夏王朝的人物,并非胡人。为了表现羯胡将遭遇灭顶之灾,这些图像人物先变为“胡状”(估计主要是高鼻深目),再将头缩进了肩中。八年之后的350年,冉闵发动的大屠杀中,“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于是“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人。”屠杀的对象被限定为胡羯,而赏功的标准是斩“胡首”。一个首级如何判定是不是胡?自然只能看面貌特征,故而“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东汉以来胡人形象被标签化为高鼻深目多须,使之成为异族、他者的可视化特征,文化与政治性的族际差异走向了种族化。石赵统治之下“讳胡尤峻”,同时又给予羯胡以特权地位,既是对“胡”之污名化的反抗,又进一步强化了石赵统治集团与“胡”的关联。长期以来的歧视、永嘉之乱后的仇恨、加之石虎残暴统治带来的积怨,便一同聚焦于一个具有此种可视特征的“异族”,最终迎来了这场大屠杀的悲剧。

左图:霍去病墓的马踏匈奴石雕、右图:唐三彩胡人俑
三、创业伙伴十八骑
在社会流动走向固化的两晋时代,石勒从奴隶到皇帝的经历是一股逆流,要打破华夷、贵贱双重壁垒。即便在十六国群雄中,石勒也是一个特例。刘渊有五部匈奴的强大背景,慕容、拓跋数代称雄塞外后才进入中原,就连苻、姚两家,也是氐羌中的大酋豪,又在石赵之世成为被徙往关东的关中豪族领袖。唯有“小胡”石勒,算是真正的白手起家,在创业建国过程中不仅没有部落的支援,甚至连家族也无法提供多少支持。
石勒初期的创业伙伴,是颇具传奇色彩的十八骑。据《十六国春秋·后赵录》,与十八骑相遇相结时,石勒正处于生命中最低谷的时期。石勒出生于公元274年,即西晋武帝泰始十年。四年之后西晋灭吴,走向其昙花一现的全盛期。太安年间(302-304)并州饥乱,石勒和很多胡人一起,被他们的父母官并州刺史司马腾掠卖到太行山东的冀州换取军粮,在路上“两胡一枷”,还不时遭到殴打,饥病交加,差点死在途中。《石勒载记》写“时年二十余”,其实已经年近三十。石勒死于公元333年,享年六十,前面三十年在并州地区当着为人傭耕的雇农,后三十年在河北地区征战创业,而以319年称赵王建国为标志,后三十年也被分成大体对称的两段。无论如何,30岁左右的这场变故,让石勒从自由民沦为了奴隶。到达河北之后,他被卖到茌平县的师懽家为奴,很快声称自己经常听到鼓角之声,师懽听说后,“奇其状貌而免之”。328年时,这位师懽以茌平令的身份向赵王石勒献上了一只黑兔,被大臣解读为水德的祥瑞,根据五德相生说,西晋为金德,继晋而起的王朝应该是水德。此前石勒一直以赵王若干年纪年,借此机会才创建年号,改元太和元年,向着称帝又迈出了一步。此时距离师懽放免石勒过去了二十五年,师懽成为茌平令,显然出于石勒的提拔,厚待在困难时期帮助过自己的故人,是石勒的美德之一。这种美德按当时观念应归为“义”,义是所谓任侠的关键,而与十八骑的结合最初便是一个恩义式的任侠行为。那年石勒刚刚被师懽免除了奴的身份,重获自由,一面以善相马的才能依附于邻近的马牧率汲桑,一面仍需四处傭耕以维持生计。在邺城附近的临水县当雇工时,又被一股游军所囚,眼看要重演被卖为奴的剧情,他却设法逃脱出来,据说有神人化为群鹿吸引军人注意力帮助了他。一无所有的石勒,
遂招集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骑为群盗。后郭敖、刘徵、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又赴之,号为十八骑。
这一切都发生在303-304年之间。犹如芒砀山的刘邦,抑或梁山泊的宋江,石勒就此踏上了金戈铁马的后半生。
这十八骑都是些什么人呢?其中有几个姓氏一看就很特别,比如夔、支,基本可判定是来源于西域的姓氏。夔氏据说来自天竺,支则是月氏(贵霜)人的汉姓,汤球辑本《后赵录》中有《支雄传》,也说“其先月氏胡人也”;此外呼延氏是匈奴贵姓,常与单于联姻;刘虽为汉姓,但已有大量匈奴、屠各人改姓了刘(唐长孺《魏晋杂胡考》)。此外,一些看似平常的姓氏,如张、王,也未必都是华夏,前文提到过石勒与之结拜兄弟的胡部大张㔨督,就是一个采用张姓而仍用胡名的胡人,与之类似的还有一个乌丸酋长张伏利度。还有十八骑排名第一的王阳,赵国建立后担任“门臣祭酒”,专理胡人辞讼,后又以此职专统六夷辅佐太子石弘,故而王阳大概率也是胡人。当然这不是说十八骑都是胡人,其中一定也有非胡人,事实上他们的族属来源十分复杂。籍贯地域也是一样,石勒来自并州,而桃豹为范阳人,其他人来历不详。地域与族属并非凝聚他们的决定因素,当然也不构成阻碍。在乱世中相似的经历与处境,以及雄武善骑射的作战能力,让他们在邺城以东的山泽间聚集起来。这批人数不多的“群盗”,很快奉马牧率汲桑为首领,又随汲桑加入西晋成都王颖故将公师藩的队伍,在公师藩、汲桑相继败亡之后,再投奔匈奴五部的领袖、曾同属成都王颖阵营、此时已称汉王的刘渊,由此汇入永嘉年间北方巨变的洪流。
十八骑不只是石勒创业初期暂时的伙伴,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石赵建国之后仍然身居要职,可以说构成了石赵政权中功臣集团的重要部分。309年石勒被刘渊任命为安东大将军、开府时,
以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为将率。
这是他手下的核心武将名单,其中除了孔苌,都是原十八骑的成员。十八骑中未列入这个名单的人,很多在此后依然活跃。比如郭黑略,在311-312年葛陂之战期间仍在军中,并在此时向石勒引见了佛图澄。再如张越,后来成为石勒的姐夫,但因在与诸将赌博时戏言忤勒,正好被石勒撞见,获罪被杀,时在316年左右。又如郭敖,330年石勒称赵天王时,以左长史郭敖为尚书左仆射,居于整个官僚队伍的“端右”。
十八骑作为功臣集团的代表,在赵国建立后的政治中表现如何?与大多数十六国政权一样,石赵在权力继承方面屡屡遭遇致命性的危机。众所周知,石勒临终安排了其子石弘继承皇帝之位,但不出两年就被石虎篡夺了。石虎从辈分上本是石勒的侄子,但“勒父朱幼而子之”,当时就有人说他是石勒的弟弟。当石勒被掠卖到河北时,石虎与其他家人仍留在并州。311年,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为了争取石勒,特地将勒母王氏与石虎一起送到了葛陂,这年石虎17岁,石勒38岁,两人相差21岁。而后来立为世子的石弘,要到314年才出生,又比石虎整整小了19岁。石虎在投奔石勒之后,很快表现出勇猛善战同时也暴戾残忍的性格,屡建军功,成为石勒麾下的得力战将。与慕容、拓跋、苻氏、姚氏等宗族殷繁、父子兄弟子侄一齐上阵的局面不同,小胡石勒缺乏家族支援,石虎就是唯一参与到早期艰难创业历程的石氏家族成员。石虎曾经骄傲又愤懑地对儿子说:
主上自都襄国以来,端拱指授而已。吾躬当矢石二十余年,南擒刘岳,北走索头,东平齐鲁,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每一忆此,令人不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
传弟还是传子,是许多乱世政权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尤其对于缺少嫡长子世袭传统的胡族来说,石虎更有理由要求继承大位。然而石勒另有打算,积极扶持自己的儿子石弘、石宏,先后将统领六夷的大单于一职交给这两位十多岁的孩子,让石虎尤其感到气愤。在这场涉及接班人的斗争中,功臣元老们的态度无疑十分重要,十八骑作为石勒最早的恩义伙伴,如何选择其立场呢?
十八骑元老中,确有人被安排到了石弘一边。石弘幼年时,石勒除了安排一批华夏文士教以儒经、律令,还专门“使刘徵、任播授以兵书,王阳教之击刺”。刘徵、王阳都是十八骑成员。在石勒称赵王的第八年,即326年,石勒强迫石虎交出镇守邺城的权力,“以世子弘镇邺,配禁兵万人,车骑(虎)所统十四营悉配之,以骁骑领门臣祭酒王阳专统六夷以辅之。”石勒派去执行这一重大任务的,正是王阳,他名列十八骑首位,又长期担任门臣祭酒负责对“胡人”的管理,既指挥禁兵,还专统六夷,又曾教石弘击刺,无疑是太子党中的重臣。此后他的名字再也没有见于史料,下场不明。另一位十八骑成员郭敖,在330年已是尚书左仆射,地位也很高,在334年,即石勒死后的第二年、石虎即将废除石弘前夕,被派往关中作战,在马兰山军败于羌酋薄句大,石虎“闻而大怒,遣使杀郭敖”。按郭敖的资历,一次战败即被处死颇不正常,很可能他也是支持石弘的一派。这一批旧臣在石虎夺位前受到排挤,石勒刘皇后言“先帝旧臣皆已斥外,众旅不复由人”,大概指的就是这种状况。
然而,十八骑成员颇有些仍活跃于石虎统治时期。曾与王阳共任门臣祭酒的夔安,在石虎初即位就被任命为侍中、太尉、守尚书令,成为朝臣中地位最高的人,领衔劝进石虎称尊号的也是他。340年九月夔安死,被东晋一方当作三月“荧惑从行犯太微上将星”的应验,可见其地位。338年,石虎讨伐辽西鲜卑段辽时,四大主将中的两位便是桃豹与支雄,桃豹于下一年去世,身份是位极人臣的太保(或许是死后赠官)。郭黑略在石虎后期曾率军与长安北山的羌人作战,几陷险境,佛图澄以佛法为之祝愿。刘徵从323年起担任青州刺史,一直到石赵灭亡前夕回到邺城。还有逯明,345年石虎大规模抢夺百姓妻女充后宫,激起民变,“金紫光禄大夫逯明因侍切谏,季龙大怒,遣龙腾拉而杀之。”最晚的一条记载是赵鹿,在350年冉闵之乱中,他以太宰身份率领一批军队奔往襄国。这里举出的已经有七人,他们在石虎统治期都身居高位,至少未遭明显的打压,考虑到十八骑中一些人可能已先于石勒去世,以及史料记载的不完整,这一比例可说非常之高了。
至此可以推论,大多数在石勒后期尚存的十八骑等功臣元老,支持或默许了石虎对石弘的夺权。何以如此?恐怕其中有超出个人忠诚品质之外的原因。如前文所引石虎的怨言,在定都襄国之后,石勒已经较少亲自率军征讨,在前线指挥军队的常是石虎和其他功臣武将。石虎在军队中的威信和人脉,无疑是石勒之下一人而已。反观石弘,一方面比石虎年轻19岁,没机会参与建国时期的战争;另一方面石勒更加注重他的文化素养,安排了一大批儒士去教他经典文化,把他培养得“虚矜爱士,好为文咏,其所亲昵,莫非儒素”。真正与石弘深度绑定的,是程遐、徐光、张跃等一帮文臣谋士。石虎和石弘之间,隐然是幼弱与资深、武功与文治、胡夷与华夏之间的分歧,十八骑等胡族居多的军功武臣,选择支持石虎,并不十分让人意外。

北齐娄睿墓壁画(局部)
四、胡人可为天子乎?
小胡石勒凭借卓越的政治军事能力,在永嘉乱世一步步成为太行山以东最具实力者,其后赵王、赵天王、赵皇帝一路升级,并没有遇到真正的障碍。天下固由马上得之,石勒深谙此理,当319年匈奴刘曜中途追回册封石勒为赵王的使节时,石勒愤然说道“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经过一番准备,当年就正式称了赵王,与刘曜彻底摊牌。然而自古无胡人为帝王的说法言犹在耳,谁不愿意做一个名正言顺具有合法性的帝王?石勒和他手下的文臣们如何解决这个合法性困境呢?
最老套办法的宣扬应符受命。在称赵王之前,照例要有群臣劝进。石虎领衔的劝进上疏中写道:
伏惟殿下天纵圣哲,诞应符运,鞭挞宇宙,弼成皇业,普天率土,莫不来苏,嘉瑞征祥,日月相继,物望去刘氏、威怀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静,星辰不孛,夏海重译,天人系仰,诚应升御中坛,即皇帝位。
这里提到的符瑞、征祥,就是像师懽所献的黑兔之类的东西,各地争着制造这些符瑞,日月相继地送到石勒面前。这是基于汉代就已盛行的天人感应思想,王莽禅代时做了第一次大规模运用,此后王朝“禅让”之际,都成为标配的程序。越是对自身合法性不自信的统治者,比如孙吴末代君主孙皓,越热衷于用这些符瑞去证明天命在己。石虎当上“大赵天王”后,有人在武乡获得一枚玄玉玺,方四寸七分,龟纽金文,送到邺城。夔安等大臣趁机劝进:
大赵水德,玄龟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宝也。分之数以象七政,寸之纪以准四极。昊天成命,不可久违。辄下史官择吉日,具礼仪,谨昧死上皇帝尊号。
简直严丝合缝,天命是不是表达得太直白了呢?原来这枚玉玺是在石弘统治期间,石虎专门制造的。虽然在夺位过程中没用上,仍不妨在之后来个锦上添花。
然而符瑞谶纬之类为前代华夏君主所惯用,其虚伪性也并不全然是秘密,关键是并不能正面回应胡人能否为天子的问题。此时流行的另一个说法正可补充这一漏洞。继王浚、刘琨之后,石勒最后消灭的西晋北方遗臣是邵续。当石季龙将邵续俘获送到石勒面前时,勒命徐光责让他为何负隅顽抗不早归顺,“以夷狄不足为君邪?”邵续敏锐捕捉到了此中机锋,在一通常规的忠臣事主无二心的解释之后,说道:
周文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帝王之兴,盖惟天命所属,德之所招,当何常邪。伏惟大王圣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耻隔皇风……
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古代华夏最伟大的圣王都能出于四夷,谁还能说胡人不能为天子呢?这真是打破天命观之华夷壁垒的绝佳论证。无独有偶,在石勒之前,304年刘渊决定自立建国时,就向群臣说过“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稍后慕容廆也说过同样的话。士族渤海高瞻降于廆,却不愿接受官职,慕容廆对他说明自己的志向是匡复晋朝帝室,收复二京,接着说:
君中州大族,冠冕之余,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
三份如出一辙的论证说明,这一说法在彼时确实一定程度流行着。稍往前追溯,在刘渊之前,这样的话已出于西晋时期的华谭之口。华谭原为孙吴人,晋灭吴之后到洛阳做官,屡屡受到中原士族的歧视。华谭在秀孝对策中拔得头筹,博士王济却嘲笑说:“君吴楚之人,亡国之余,有何秀异而应斯举?”谭答曰:
秀异固产于方外,不出于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贝,生于江郁之滨。夜光之璞,出乎荆蓝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于东夷,大禹生于西羌。子弗闻乎?
三国分立之时,在宣传当中,中原的魏晋政权常常将吴、蜀称为蛮夷,以此解决大一统尚未实现的尴尬。此前吴蜀人士对这一攻击的反驳,都是在证明本地名列东汉十三州,绝非王化禹域之外。惟华谭采取退步反击的策略,就算吴是蛮夷之地又如何,文王、大禹还不是出于东夷、西羌?这段对话在当时可能广为人知,正在洛阳当质子的刘渊一定有所耳闻。追根溯源,此说最早见于西汉初年陆贾的《新语·术事》,先秦文献中说文王生于西夷是主流,《新语》的东夷说比较小众,何以在西晋十六国时如此流行,也是很有趣的问题,为免过于枝蔓,这里就不讨论了。
获取天命的办法还有很多,比如占领前代王朝的都城,尤其是洛阳城。洛阳是东周、东汉、魏、西晋的都城,又戴着天下之中、周公营建的光环,此时已是无可置疑的神圣之都。十六国政权积极争夺洛阳,东晋的北伐也常以收复洛阳为主要目标。(参看胡鸿:《天下之中的苦乐悲欢》,收入耿朔、仇鹿鸣主编《问彼嵩洛:中原访古行记》,中华书局,2019年)321年,即石勒称赵王的第三年,便下令在襄国“拟洛阳之太极,起建德殿。”又“徙洛阳铜马、翁仲二于襄国,列之永丰门”;四年后再“命徙洛阳晷影于襄国,列于单于庭”;在正式称帝的331年,又起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这原是汉晋洛阳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三件套;至此仍觉不够,甚至有移都洛阳之意,先命洛阳为南都,设置相应的官署。搬运洛阳的帝都旧物,似乎就分享了洛阳的正统性,这与秦始皇搬运九鼎异曲同工;对于无法搬运的宫殿、礼制建筑,就仿而造之;得陇望蜀,最终还是难以抵御定都洛阳的诱惑。洛阳就像一块饱含正统性的磁石,时刻吸引着那些对天命不够自信的北族君主,直到496年,北魏孝文帝终于完成这一近二百年的集体夙愿。
在塑造正统性的武器库中,“历史”从来不会缺席。石勒不识字,却并不缺乏历史感。319年,石勒称赵王之后的第一批命令中,就包括:
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
上党公、大将军、大单于是石勒从匈奴汉国先后获得的官爵,到后期是三者兼任的,分开撰述他在不同身份上的作为,以合成一部完整的建国史,充分显示了他对修史的重视。赵国建立之后,日常记注和国史撰述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后世所见《十六国春秋》和《晋书·载记》中英明神武的石勒形象,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史臣“润色鸿业”的结果。
除了在乎自己高大的历史形象,石勒大概确实也是一个历史爱好者,如果他有一个偶像,那估计就是刘邦。不少人都知道《世说新语·识鉴篇》中的故事:
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
在基于石赵国史的《晋书·载记》中,又补充说“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用耳朵听书学习历史,石勒倒是今日诸多音频课爱好者的先驱。他最爱听的,大概就是刘邦建立汉朝的故事。这也不难理解,从布衣到天子,没有贵族背景,没有血统凭借,没有家族支援,与石勒如此相近的前任帝王,仅刘邦一人而已。崇拜也好,借鉴也罢,刘邦的故事石勒一定听得滚瓜烂熟。所以我们看到,刘邦特意给素所不快的雍齿封侯,石勒也找来少年时为抢沤麻池经常与他打架的李阳,拜官赐宅;石勒回到故乡武乡,发令免除其赋役,令文开头就说“武乡,吾之丰沛”;第三次攻下邺城时曾征辟一位西晋遗臣赵彭,拟任魏郡太守,赵彭婉言拒绝,石勒默然不快,气氛顿时紧张,谋臣张宾赶紧说赵彭“以将军为高祖,自拟于四公,所谓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将军不世之高”,于是石勒大悦;石勒妻刘皇后,本为匈奴后部人,曾袖剑手斩反臣,史书便说她“有吕氏辅汉之风”。明白了这些,便更好理解那段石勒自比古代帝王的著名故事:
勒因飨高句丽、宇文屋孤使,酒酣,谓徐光曰:“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对曰:“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荦超绝魏祖,自三王已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其群臣皆顿首称万岁。
遇到刘邦,就北面而事之,与韩信彭越争做开国功臣;遇到刘秀,与之并驱逐鹿,尚不知胜负如何。所谓“在二刘之间”不过是谦辞,石勒内心之中,其实早已自比于刘邦了。
无论举文王大禹,还是向往洛阳,抑或自比刘邦,合法性的论证仍然没有跳出两汉魏晋以来的华夏政治文化,华夷秩序的魔咒仍在其中,无法完全解除。在十六国时代,这一问题近乎无解。然而正在此时,变化的契机已经悄然出现,那就是佛教日渐加速的传播及其对政治的介入。后赵时期,佛教在中国北方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流行,石赵治下的百姓营造寺庙,相竞出家。于是,石虎下令料简,将不合法的出家者变回国家编户,引起一场朝堂上的争论:
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龙以澄故,下书曰:“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
当大臣祭出华夷之防,将佛作为“外国之神”加以反对时,石虎敏锐意识到其中的问题,一反此前的态度,在诏书中他不仅承认“出自边戎”,而且肯定“佛是戎神,所应兼奉”,从此夷、赵百姓事佛便成为合法行为了。石赵国祚短促,佛教在政治中的作用未及发挥。此后,历十六国至南北朝隋唐,佛教日渐兴盛,成为“征服中国”的第一信仰,跳出华夏天命话语的佛教王权观,诸如转轮王、菩萨皇帝等,也成为皇权合法性论证的新途径(参看孙英刚《转轮王与皇帝:佛教对中古君主概念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1期)。胡人可为天子乎?旧问题终于有了新的答案。当然,这个答案,石勒永远不会知道。
原地址:https://www.chinesefood8.com/9085.html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