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婧/口述 澎湃新闻记者 王芊霓 实习生 赵梦圆/整理
传统的“粉丝-偶像”关系大多遵从异性恋框架下的“男女朋友”这一欲望模式,而“妈粉”这个群体呢?他们是因为“我想给你当妈妈”,所以成了“妈粉”吗?在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徐婧与其研究生孟繁荣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她们发现“妈粉”的追星行为和现实中的“母职”有着奇妙的呼应,她们把“妈粉”围绕偶像的日常称为“数字化抚育”。
澎湃新闻对徐婧进行了采访,以下是徐婧的口述。

徐婧 受访者供图
“妈粉”的问题建构
我是徐婧,是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的老师。我读书的专业背景比较复杂,学过社会学,学过文艺理论,现在是传播学。我关注的是媒介如何呈现社会结构里面的“社会性别”,性别视角又是怎么在媒介产品中被体现的,粉丝文化是个很好的切入点,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亚文化的小众领域,但正是在很具体、琐碎的的关系里,我洞察到一些有趣的问题。
我的这项研究的前期观察从2019年就开始了,正式的调研是在2020年9月到2021年6月间进行的,研究使用网络民族志,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对“妈粉”群体展开资料收集,并对这些材料进行交叉分析。
我的28位研究对象(包括两名男性)来自多个明星的粉丝群体,包括韩国男团BTS、时代少年团、王一博、郑云龙、阿云嘎等等,年龄在19岁到45岁之间均有分布。本研究的被访者主要生活在上海、杭州、西安和广州等城市;主业也各不相同,有大专院校的大学生、研究生,有高校教师、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还有些人是企业中层、高层管理人员。她们作为妈粉的日常,主要是在所粉偶像的网络粉丝社群中,查收偶像最新咨询,或响应“大粉”动员打卡、反黑,参与增加流量的各类数字追星实践。
在收入方面,被访者里的一部分尚无独立经济能力,但仍会将日常生活费用中的一部分用于稳定的追星消费;另一部分在社会中具有稳定甚至较好的收入水平。“妈粉”们“氪金”所花费的金钱,是她们收入的6%到13%,但有“妈粉”表示,自己为偶像所花费的金钱很难用此种计算法衡量:有人表示自己常有大宗同款支出,如不是偶像同款也并不会去消费。总之,本研究中的“妈粉”群体是以女性为主,年龄、职业多元,具备一定经济能力,有一定的追星年限。
我个人同时具有粉丝和研究者的身份,所以我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我希望自己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还是能够时刻保持学者的独立性和尽可能的客观。我做这项研究也并不是要为粉丝群体“正名”,我更希望尽量把粉丝群体内部的多样性展现出来——任何社群的凝结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我的初衷就是将“群体”抽丝剥茧,比如:在粉丝群体内部有各种类型的粉丝,妈粉这个群体和其他类型粉丝群体的区别是什么?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为什么如此这般在线上生活,这就是数字媒介实践研究要做的,这种实践包含着实践者丰富的情感、诉求、欲望的呈现。在线上社群中观察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到“妈粉”这个群体是可以、且应该被进一步探索和解释的一种身份指称现象。这样一种身份的形成过程与母职存在一定的呼应和关联,是阿尔杜塞意义上的一种“询唤”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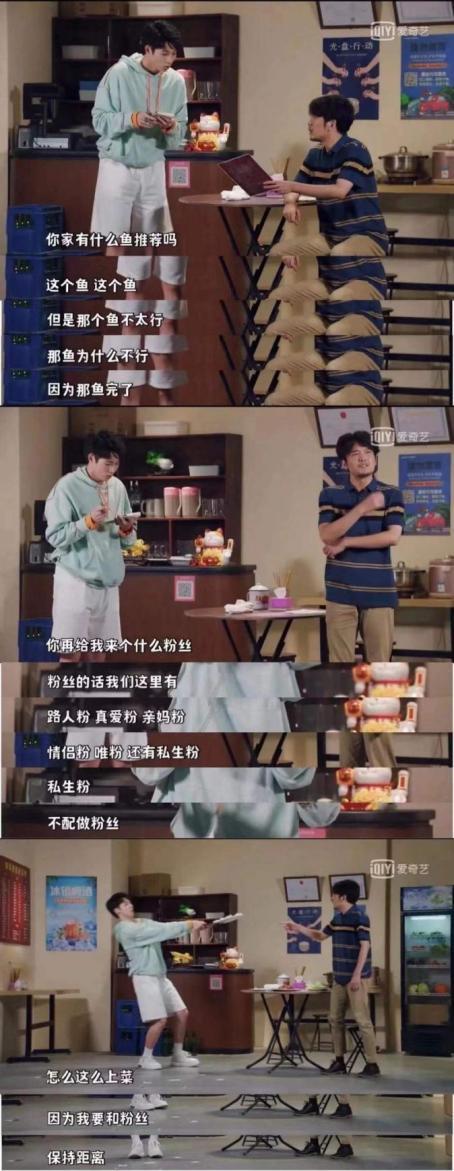
充满谐音梗和饭圈言论的喜剧《偶像服务生》
“妈粉”的两大特征
“妈粉”的一大特点,是自己对喜欢的明星并无肉体欲望的投射。她们是在寻找和界定一种难以用异性恋框架界定的情感模式时,找到了“妈粉”这样一种身份。因此,“去性化”也成为了妈粉与其他类型粉丝最重要的一个区别。
但从受访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妈粉的身份认同并非一成不变,她们也会因为偶像偶尔展现出的性感外形或突出霸权男性气质时,而产生与以往不同的情绪,这时“妈粉”和“女友粉”的界限就不那么清晰了。有一个访谈对象说,自己之前很喜欢的明星,一直觉得有幼童的那种可爱和纯真。结果突然有一天他换了一个全新的造型,跟此前完全不一样了,被塑造成一种性感的、具有性张力的模样。她说,“瞬间就母爱变质了。”但很多人向我强调:对于妈粉而言,“母爱变质”只可能是一瞬的,针对他的这一个形象、这一个身体状态,然后很快就会回到妈妈去性化的状态中去。

脱口秀节目中,王勉弹唱了一段关于饭圈女孩的故事。
因此,妈粉并非一个边界清晰且稳定的身份类型,而是一种关系性的动态的变化过程。粉丝有主体性,他们会将偶像展示在人前的身份与自己的感知进行选择性建构。极强的身份流动性与包容性,就是“妈粉”对母职符号能指的直接挪用而导致的。
“妈粉”对母职的认同
我访谈中有一位男性妈粉,他说,我之所以觉得我也可以是妈粉,是因为我的妈妈就是这样爱我的,那么我觉得我对偶像的情感也是这样,那么我就可以定位自己为她的妈粉。我对她没有其它的诉求,我想看着她觉得很快乐,然后也很无私,我也不期待她对我有什么回应。然后他问出了一个经典的反问句,“你觉得互联网上有谁会去做别人的爹?”。是的,为什么互联网中的追星男女,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纪稍长的,为什么当大家想去形容一种去性别化的、去欲望化的呵护、照料,这样一种无私情感的时,首先借用的亲属称谓是“妈妈”? 因为在我们的历史语境下,东亚内部的家庭秩序及其表征的母职的性别秩序,成为了妈粉操演的主要的意识形态资源。而那位男粉丝所言的,不愿给人当“爹”,是对模拟、操演东亚家庭中的父亲角色的拒绝。
成为妈粉之后,她们被“母职”所询唤——也开始以传统的母职意识形态来要求、约束、规范粉丝行为。比如说也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访谈对象里有一位很明确地提到了,因为她自己有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她说自己对偶像的态度就跟对小孩一样,首先希望他健康平安,但是也希望他未来学业、事业上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当你去使用一个“概念”或称谓去称呼自己时,就会不知不觉的开始用传统意义上“妈妈”的角色来要求自己。
妈粉对偶像的业务能力、事业心、上进心、相关话语权与社会地位等方面尤为在意。对于偶像谈恋爱、犯错误,妈粉反而比较包容,但她们一致认为,当偶像表现出在事业上不够努力,她们的爱就会大打折扣。在对偶像“望子成龙”这方面,现实母职和虚拟母职达成了微妙的联结。
一方面是对母职的高度认同,另一方面是不断操演“传统母子关系”并获得回应,这就是妈妈粉的自我认同过程。他们也通过消费来制造一种获得感,跟自己的偶像建立连接。我的访谈对象就告诉我“我买的越多,我可能就能帮到他越多”。品牌方会觉得该偶像粉丝消费能力强,就给他更多更高级的代言。当然,最终是这套商业盈利的逻辑,决定和形塑了当下资本、平台、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
在当前饭圈整顿的大政策之下,流量艺人就特别需要去证明自己的粉丝群体是安全的、高素质的,是不需要被治理的。所以某位偶像的“妈妈粉”自称“博士二孩妈”(注:人均博士学位,育有二子的中产女性粉丝形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生产和制造出来的。
“妈粉”尝试去超越旧框架、定义一种新型的粉丝偶像关系,是一群女性在自己数字化行为实践的过程中对某种旧框架的挣脱,想用一种全新的东西来界定自己。虽然这种界定的行为也难逃窠臼,也没有办法去摆脱娱乐工业体系的制约,但至少在性别秩序层面向前走了一步。不要说女生追星都是无脑的,都是女友粉,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情感关系很多元,我们也在尝试去找到更新的性别关系或者欲望关系,来与我们自身的情感诉求进行互动。

人民视觉 资料图
【对话】
澎湃新闻:这种“数字化抚育”看上去远比现实世界中的母职要轻松很多,用这样的术语是不是会显得现实中的母职太轻飘飘了?
徐婧: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数字化抚育也是劳动,因为它也付出时间和金钱,也有情感的互动和贡献。我个人愿意把它定义为一种关于母职理论积极的进展。当然,我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些理想主义。
包括我自己在做所谓数字化抚育的时候,也曾设想过,我去做这样的一种建构:描绘母职的新进展,是否也是一种帮助解除“母职与女性天性绑定”关系的努力?至少在理论层面,也许是对陈旧权力结构的动摇。当然,现实的中抚育付出了更多的劳动、情感,其中包含了更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秩序。
澎湃新闻:你通过研究这种妈粉的“虚拟母职”,也想试图解构现实中的“母职”的概念?
徐婧:是的,这至少说明“母职不是一种天性”,也并不必然地与生育行为一一对应,它证明了母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建构。“妈粉”并不是生理上的母亲,但是通过这种数字化的操演,无论是花钱,还是精力的投入,都是可以跟传统意义上的母职产生共振。
我把这个现象起名为“数字化抚育”,实际上我就是想要去讨论它会不会是母职的一种新的发展。这种替代性的情感出现之后,有没有一种可能,未来女性想要体验或进入母职,真的不需要以生育为连接了。
澎湃新闻:你的研究对象的生育意愿和她们的妈粉身份是否有什么相关性?
徐婧:我访谈的28个人里,有22人未婚未育,其中有11人明确表达对婚姻和生育都没有太多欲望和诉求。当然,也有人虽然现在这样跟你讲,再过几年她可能就去结婚生子。但至少在“妈粉”这样的一种反复的母职操演过程中,她认为暂时的抚育的情感及其衍生的劳动、劳动的获得感都已经得到满足,妈粉的操演可能只是未来数字化抚育的形态之一,当它被整个社会更加广泛的接受和承认时,或许一名女性,是否履行母职、如何履行母职,都会成为一种可以在以“血缘为基准的家庭空间”和“以情感为基准的虚拟平台”中转换自如的操演。
责任编辑:梁佳 图片编辑:金洁
校对:徐亦嘉
原地址:https://chinesefood8.com/1633.html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上一篇:虎宝宝霸气响亮的男孩名字
下一篇:一个网红主播在家中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