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声喧哗
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播客小声喧哗四位主播对纽约时报杂志席卷互联网的一篇文章“Who is the Bad Art Friend”(翻译版本名:《肾、小说和女作家之战》)有着四种不同的理解。小声喧哗借此机会探讨社交媒体大环境下善举和善举背后的动机,女性作家的冲突为何被认为只是女人之间撕头花的故事,以及补充了中文互联网对本文的理解缺乏的一些关于美国社会的语境。
本文为小声喧哗播客与澎湃新闻合作刊发的文字稿,由澎湃新闻()记者龚思量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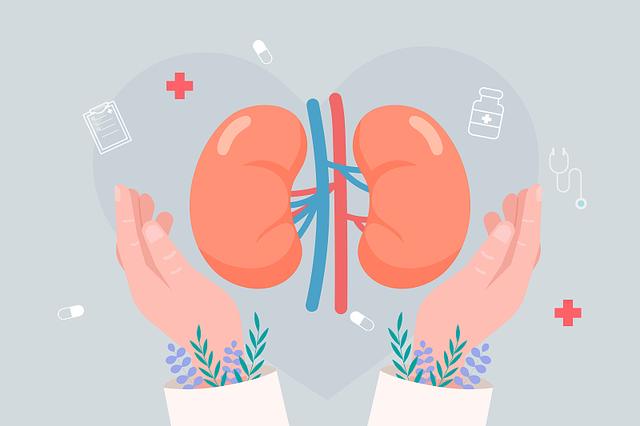
刁刁:这是一期相对而言比较特别的节目,因为我们平常都是从电影或者电视剧出发来描述一个社会现象,但这次我们想从一篇文章所引发的席卷社交媒体的关于流行文化、关于当代社会的讨论来聊聊这期节目。
这篇文章叫做 “Who is the Bad Art Friends”,《谁是糟糕的艺术家朋友》,是罗伯特·科尔克(Robert Kolker)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的万字特稿,描述了两位作家Dawn Dorland和Sonya Larson之间关于名誉艺术创作和道德,并且席卷了互联网的“血”战(因为真的有人流了血)。在那个周末,每一个英文社交媒体都在讨论这个故事,每一个群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钱娟:所以我们决定把散落在各个角落的讨论搬到播客上来,因为这个故事涉及到了很多主题。然后在讨论之前,我觉得可以先给没有看过原文或者没有看过中文翻译的听众来总结一下这个故事。
在2015年,一名叫Dawn的作家,决定把她的肾脏进行非定向捐赠,不是捐给她的熟人或者是亲人,而是给一个完全没有见过的陌生人。在她决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她拉了一个私人的Facebook群,然后在群里发布了她准备捐肾的整个心路历程,里面还包括一封她写给未知的受赠人的、非常感情充沛的信。这个群里面有很多她的朋友,其中就有故事的另一个主角Larson。Larson也是一个作家,是Dawn在波士顿的一个写作社群(Grubstreet)遇到的一个作者。
大概在一年以后,Dawn从第三方得到消息,Larson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小说里面有关于肾脏捐赠的情节。捐肾的这个人是个挟恩图报、有白人救世主情节的人物。这个人不能说是一个坏人,但至少是个烂人,而且这个人想要的回报不是金钱而是赞美,要求对方对她有一种心理上的服从和崇拜。Dawn因此感到非常受伤,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里包含了经过了轻度改编的,Dawn之前在Facebook群组里发出过的那封信,所以Dawn认为这里存在抄袭的问题。
之后这几年,Dawn陆陆续续地联系了Larson,问她为什么就没有跟自己打声招呼就拿自己的故事写小说,但几次邮件交流都非常得不愉快。随着Larson这篇小说眼看要大获成功,甚至可能为她的事业开启一个新的篇章,Dawn决定要把事情闹大,于是她们两个就开始对簿公堂。
Dawn最主要的一个指控,就是指责Larson抄袭了她的那封信。Larson则认为Dawn是在诽谤自己,并指出在做艺术创作时,拿生活中的人和事进行加工是最正常不过的。
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她们已经上了法庭,所以Larson和她朋友在群里说Dawn坏话的聊天记录也被传唤,所有人都能读到这些记录。在这些私信里面,Larson对Dawn的态度非常刻薄,而且她承认了自己抄袭,她说自己想要改掉那封信里面的话,但这封信写得实在是太好了,不舍得不用(“too good not to use it”)。《纽约时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写悬疑小说出身的,他非常擅长去操纵读者的视角和感受。所以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会感觉好像自己一会儿站在一个主角那一边,过了三段就支持另外一个主角,不停地在左右摇摆。
而且一般来讲我们四个人对一件事情的理解还比较相似,但看完这个故事以后,我们的第一印象、注意到的细节都完全不同。其中的不同似乎是自己个人经历、个人看法,甚至是很多不同的社会文化议题的投射,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把这个话题掰开来讲一讲。
所以我想先听一下你们在读完这篇文章,还没有去看网上的议论,也没有查各种资料的情况下,你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刁刁:我的感觉是,这是一个关于人与人关系里那种非常细微的、关于做善事的权力关系的故事。就像你刚刚说的,有的人是会挟恩图报,有的人会希望从别人身上获得认可和服从,完成一种交易。Dawn在捐献之前开了一个Facebook Group,拉这个群的目的是分享她捐肾的心路历程,她当时就注意到了Larson没有给她点赞,她的反应是写了一个邮件,在客套了几句之后她说,我觉得你应该知道我在这个夏天捐了一个肾脏吧?(I think you are aware that I donate my kidney this summer,right?)后来她去参加这群写作者聚会的时候,会记得聚会里没有人提到她捐赠的事情,她的原话是:难道作家们不在乎我捐肾这件事情吗?(Do writers not care about my kidney donation?)我还以为作家是一些相对而言很注重社区服务(service oriented)的一群人。
我看到这段时,就感到非常愤世嫉俗、非常犬儒。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尤其是在社交网络上做好事是会带来一些权力的,然后这种权力会让我很警惕。Dawn表现出来的,是她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做好事的社交价值。她有一种预期,在做完好事后,身边的人以及社会上应该能给她一定的关注和赞美。这让我对Dawn感到一种很强烈的不信任。
如果这种权力落在了一个“知道这种权力,且不介意行使这种权力”的人手里,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的社会会原谅所有比救人一命更轻的侵犯。所以我当时看完文章后,就带着这种感觉去看了Larson写的故事,叫做“The Kindest”《最善良的人》。
文章本身还行,它讲的是做善事之后的小九九。亚裔女主角春桃接受了一个深陷救世主情节女性Rose的捐肾。文章的视角完全是从春桃这里展开的,她失去肾是因为她酗酒还酒驾,她获得肾之后还在喝烈酒,整个人的性格都非常刻薄。对Rose善举的描述也非常刻薄。我们跟着春桃的视角来看,Rose的性格特质基本上就只是自以为是、自我感动,一点点种族歧视、还有一些“PUA”,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裹胁你服从。但从读者角度上来说,我们也要意识到春桃是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unreliable narrator),春桃也试着控制我们,试着影响我们。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春桃暗搓搓地想:我本来生病快要死了,我是最被同情的人,现在她给我捐肾做了好事,大我一头了(“The thing about dying is that they commend the deepest respect”)。所以读者能看出来春桃对于这件事有一种隐秘的厌恶。
我看完这个故事之后,觉得Dawn做好事的方式表现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道德困境,然后Larson作为一个作家在观察到这个困境之后受到启发,写了一个更加极端的故事。但是Dawn觉得这是她的肾、她的经历,只有她能写,别人不可以曲解它;Larson觉得这是她想出来的故事,你凭什么夺走它,于是冲突就产生了。
Afra:我觉得这个报道其实点明了社会性和文学性之间的一道鸿沟。当小说家完成了作品,小说脱离了作者后,它就会在人们心中自行生长。可惜我们现在身处在一个高度政治化、高度极化的环境里,所以导致了人们的脑海中,这篇小说以及关于这两个女人斗争的整个叙事,长成了一个政治性的形状。
我们关注的是亚裔和白人之间的交战、阶级的复杂性(Dawn比较贫穷,Larson生长在稍微富裕的亚裔家庭、接受过比较良好教育)、女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和、作家群体的虚伪面相等等。《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也非常注重两个人交战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反而忽视了这两人文学性的人格。
我和刁刁一样,在看完报道后立刻找了小说来看。看完小说后,我一下子对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其实,“The Kindest”《最善良的人》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认为自己是个非常不完美,甚至破碎的人”,如何去和道德自处,如何去和自己自处,如何去和自己的丑恶相处的故事。
在Larson的小说宇宙中,春桃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不完美的亚裔女性形象,她自我厌恶,觉得自己对自己的生活非常不负责任,她是一个非常破碎(broken)的人。
春桃不仅仅是反射出了 Rose作为白女的虚伪和自恋,或者暗搓搓地想要通过捐肾让春桃服从,反而是Rose作为春桃的一个镜面,映照出了更加破碎的、无法和自己相处的春桃。小说里有这样一幕:已经进行完换肾手术的春桃走在一个光洁无瑕的商场里面,想给即将造访自己家的Rose买一个礼物,然后,在高洁的商场的映照下,她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这里和自己的丑陋格格不入,于是,她想赶紧离开商场回到自己的家。而自己的家在她的眼中也是一团糟,是羞于让Rose参观的。Rose的突兀造访,意味着一个全方位的对于春桃的审判的降临,或者,她的到来会逼迫春桃进行自我审判。相信曾经经历过人生低谷或者抑郁症的朋友,都清楚地知道,类似的自我审判能够触发一种自贬的病态机制,从而加害给自我本身。
春桃对于Rose捐肾这件事的道德崇高是有清楚的认知的,尽管她不喜欢Rose。而她的排斥和抗拒,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完美的人在面对“把自己淹没的善举”时候的一种下意识的逃离,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春桃和Rose都是高度凝练化的人物,分别代表着两个种族阶级,最大的差异和最幽暗的人性。
所以这就是文学的迷人之处,尽管很多人评价“The Kindest”《最善良的人》并不是一篇出色的小说,我仍认为它具备了文学的维度,将道德和自我这样的深刻主题蔓延到了一个亚裔女性的自述当中。
同时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关于Larson为什么会把自己故事宇宙中的亚裔女主角命名成一个看起来非常扁平化,甚至有些歧视意味的“春桃”。在我看来,Larson作为一个对于种族概念高度敏感的作者(在此,我承认Larson的出身和阶级以及长相的white-passing,会让人觉得她并不是一个真正在意亚裔种族斗争的人),有时候刻意使用带有殖民意味或者种族意味的人名,是想达到一个“补充”和“回击”的目的。“补充”,指的是通过把这个单薄名字代表的亚裔女性不完整性夺回的方式,去赋予“春桃”应有的人物厚度,去抵抗和回应“春桃”所经受的文学上的刻意减薄和历史剥削。“回击”指的是,通过赋予春桃完整性,而对抗“春桃”这个名字曾经所代表的不公平的一切。
Ina:我在读这篇文章之前,其实对Dawn这个角色已经有了偏见,因为知名的黑人女性作家Roxane Gay发了一条推特说“我们能不能讨论一下这篇文章?因为天哪,有些白人女性真的是太闲了”。所以,我从一开始就非常不喜欢Dawn,觉得她是一个需要身边人,乃至于全社会去关注她的人。她渴望被注意到,甚至是在她捐献之前,她可能已经脑补了自己会获得的称赞与好评。这篇文章里面也提供了这样一个背景,觉得Dawn的成长背景导致她没有受到过太多的家庭关怀,所以她做非定向捐赠,是因为她想要把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关怀给予一个陌生人。所以如果你只看她做的事情、捐赠的过程,那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决定。但是Dawn的人设非常的不讨喜,作为一个白人女性作家,在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之后开始大肆宣扬,想把目光全部都聚到自己身上,说自己怎么好,甚至还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私人群来告诉大家,这导致我当时就不是特别喜欢她。
然后这篇文章话锋一转,开始给大家看Larson的故事,同样是一位二代移民作家,华裔,还是文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在波士顿一个写作机构“Grubstreet”认识了Dawn还有其他的写作朋友。其中包括写“Litter Fires Everywhere”的华裔作家Celeste Ng。这群朋友在Larson写这篇小说时,扮演了她的支援小组,也在他们的群聊里嘲讽过Dawn的行为。他们嘲讽的倒不是捐肾行为本身,而是在Larson和她的朋友们看来,Dawn是在主动索取称赞与关注。
我读到这里,觉得可以理解Larson和群聊小组的对话,但是后来我意识到Larson有一点做得不太对,就是她从来没有把Dawn当做过朋友。她对Dawn的理解就是她是个白人女性作家,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之后就开始大肆宣扬自己做的伟大的事情。Larson是基于这么一个人设去分析Dawn的行为,所以从一开始Dawn在Larson以及她朋友们的眼里就带着这样的人设,被抽象化了。
后来看到Dawn开始采取法律措施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点越界了。Dawn觉得她是被自己以为是朋友的一群人排斥了,被她以为是朋友的人恶意妖魔化了自己的形象与行为。这当然不好,但值得去采取法律措施吗?甚至Dawn要到了Larson的手机号后不断地去骚扰Larson,出现在Larson参与的每一个写作活动,在那里默默地看着她。到这里我觉得越界了,你自己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伤害,于是你去攻击另外一个人,在什么样一个情况下这种行为是合理的?这里的边界又在哪里?
钱娟:我想先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我们在说白人女作家或者是亚裔女作家的时候会忽略一件事情,就是已经发表过的作家才是作家,没有发表过的作家是个写作者(writer)。在中文里,我们说一个人是作家,仿佛TA想写东西,TA就是作家了,但是发表过作品的作家和没有发表过的作家,这中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在Larson这样的人眼里,Dawn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她们在这个协作小组里的地位是非常不平等的。
Afra:所以就会出现Dawn非常想要进入ta们那个圈子玩的情况。
钱娟:对,我们在讨论的时候绝对不能忽略这个点。我看完这个故事以后,第一个反应: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故事,是一个痛打落水狗的故事。另外,我脑子里马上想到了他者化(other)。作者一开始花了很大的笔墨去描写Dawn这个人是多么容易被人他者化,她本来就是一个跟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感受太多、感情太充沛、经常对陌生人做一些让人家觉得比较尴尬的事情。她很容易交浅言深,容易自以为是对方的朋友。比如她以为Larson是自己的朋友,因为Larson有一次在宴会上跟她分享了一些比较私人的事情;后来互相对峙的时候,Dawn还把这事拿出来说,Larson就表示这种话我跟所有人都说,你并不是特别的。
而且Dawn的这种博爱、把心掏出来给别人的感觉,并不是因为她有足够的爱,所以她才辐射出去。反而是因为她是出自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自尊心很低的地方,是一个有很深创伤的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所以看完这前面一段描写的时候,我很不喜欢Dawn,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如果现实生活中我遇到这样的人,我应该会很讨厌她,最多就是礼貌地保持距离。甚至更可恶一点,可能在背后编排她,再加上她又是一个白人女性,所以就很符合社会对白女在长时间内烙上的一种刻板印象:有点疯疯癫癫、感情多、没事找事,可能这个标签也加重了这种他者化。
而Larson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首先她和Dawn同期加入了写作小组,结果没多久就变成了其中的骨干,很有才华。她又是一个被发表过的作家,周围的一群朋友也都是被发表过的作家,是冉冉兴起的少数族裔文坛新星,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文坛最令人兴奋的潮流,这帮人是属于所谓的弄潮儿。所以说实话我更容易带入Larson这样的心态。
我也明白为什么Dawn给陌生人捐肾这个事情,从一种很幽暗的角度来讲,其实是很令人难堪的。可能因为我的职业和他们的职业有一点点相近,所以我明白当你在社交网络上晒一个东西的时候,一个好看的姿态应该是非常轻松地、避重就轻地说自己的成就,不可以太用力地去说自己的近况,比如你捐了个肾,这是会让人非常难堪的事情。
而Dawn不仅这么做了,还把这样一个和文学毫无相关的成就专门分享给一群她以为是朋友的作家们。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很尴尬也很难受,因为这些人是不会因此对她刮目相看的。所以当她没有得到自己应有的赞美的时候,她就开始怀疑是不是这些人都不喜欢她,不想带她玩,看不起她。更可怕的是,居然有一个她自以为是朋友的人,还把Dawn写成了故事里的一个“反派”。所有后面的法律纷争也好,网上跟踪也好,都是因为Dawn咽不下这口气,最后弄到满城皆知,甚至把别人说她的坏话都一字一句的公开。
我之所以特别同情Dawn,是因为我觉得她脆弱的自尊最后让她不得不走向了一个最难堪的结局。Larson作为一个作者是完全有权利去提取生活中的人和事情来进行加工,再融入自己的创作。但我觉得沿着这条线去分析,其实避开了最核心的问题,因为这整个故事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它最后影响了两个人的职业和声誉。对我来说,矛盾的开始是Larson在她所在的新兴作家的群体里抱团,去讽刺Dawn的善举,去猜测她的动机,并且把自己的猜测写成了一种现实。这是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他者化,这是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能去洗脱的、一件非常错误的事情。因为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为了让你能够理解其他人,能够让你觉得我们之间的人性是互通的,而这件事的最反面的地方就是去他者化一个人。
而且Larson没有去改写那封信,反而是在作品里直接用到了那封信,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官司一直能打那么长时间的原因。这是因为在法律定义中,如果你用一个别人的东西,但是你把它从根本上转变了(transformative use),那就不构成抄袭。但Larson没有进行改编,并且还在短信里承认了,她觉得这封信必须要原汁原味,只字不改才是最好的。她觉得这封信太可笑了,简直就跟她要讽刺的主人公动机完全一致。这说明她真的把Dawn的善举的动机和她想要讽刺的人的动机画上了等号,我觉得这种理解太诛心了。
另一方面,Larson作为一个创作者无法跟自身的道德相处,她跟友人私下发短信的时候承认她觉得自己对Dawn的想法是很糟糕的。但最后还是决定铤而走险去用这封信,并且心存侥幸觉得自己不会被对峙。我觉得这种想法是很奇怪的,首先Dawn这样一个自尊心很低、没有被发表过的作者看着所谓的同伴获得成功,然后在她心目中Larson是踏着自己的肩膀,用自己真实的人生经历化成的作品去获得了成功,Dawn怎么可能不找Larson对峙呢?等到Dawn来对峙、要求一个解释的时候,Larson完全没有办法面对自己会成为被指摘的道德对象这一事实,所以她的道德思考也好、批评也好、犀利的讽刺也好都是躲在春桃背后进行的。因为春桃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她大可以做一个非常不完美的人,这没有关系,但Rose的原型,至少她们那个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是Dawn。所以Larson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面对一些道德选择的时候,她最后伤害了别人来保全自己。
并且最让我觉得难受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能在自己身上看到这个影子。尤其是她非常顺手地拿了一套种族相关的话术给自己的道德加码。她说Dawn来起诉我,然后想要毁掉我的职业,这正是我想要批评的这种现象,她表示这是白人打击少数族裔,或者是想要抹杀掉我们的声音。Larson用这套话术来给自己道德加码,让我没有办法相信她作为一个创作者的真诚。
刁刁:我没有想到我们四个人抓到的点和视角完全不一样。后来随着讨论的推进,更多的场外信息被加入了讨论里面,然后我个人的观点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这时候才意识到Dawn的行为是非常合理的,跟捐肾这种社会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美国现在有超过50万的肾衰竭患者,其中有9万人在等待移植。如果仅仅依靠死亡捐赠者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受捐赠的人往往是来自亲人或者朋友的捐赠。
对于我们如何鼓励更多人去捐献,其实是一个讨论了很久的医学伦理难题,因为我们不能直接给捐献者钱,如果我们给钱的话,这就相当于卖肾,就会存在一个卖肾的市场。意味着关于拐卖、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谋杀都会出现一种新的盈利模式。而这种对身体的不可逆的伤害会系统性地流向更穷困的,没有医疗或社会保障的群体。所以现在中国和美国的选择还是大量地依赖死亡捐赠者、亲友的定向捐赠和非常少数像Dawn这样的不定向选择。因为没法用金钱作为激励,政府和医疗系统只能通过宣传,让更多人觉得活体捐献是一件我也可以做的事情。
微博上有一个叫陈颀的网友,曾经在匹兹堡大学的肝肾移植中心做过一段时间活体器官捐献倡导者(independent living donor advocate)。她的职责是为这些捐赠者做一个安全网,去评估捐助者的身体状况、心理健康状况和社会支持,来确保这些捐赠者没有受到误导或强制,也不会是潜在的器官交易的受害者。
她也提到,她们对于该不该发社交媒体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医疗系统自然希望有更多的人去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讲故事的人越多,人们越会意识到捐赠其实不是一个看起来很遥远、很可怕、很激进的决定。“原来有很多人抱着和我相似的想法去做了捐赠”,这样也能影响更多的人。但另一方面,社会环境并不总是对这样的无私行为有足够包容的。当然会存在捐赠者在接受采访、走进公共视野之后遭受舆论反思的情况,因此就产生了问题——捐献这种社会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人们对于其他人做善事的动机有相对比较宽容”的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才能运转。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不希望把它放在显微镜底下来看,我们不希望做好事的人还要滚一次钉板来证明你是一个真正的好人。
我在看完陈颀的微博后才意识到,我们的犬儒、对于纯粹的善意的不信任,这种诛心的行为其实是有害的。这种想法不仅伤害到了Dawn这个具体的人,也让很多的医疗从业者担心大家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形成“器官捐赠的人是为了沽名钓誉,这些人存在一些问题”的印象。
Ina:凡是看过《机智医生生活》的朋友们都知道,肾脏捐赠对于患有肾衰竭的患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被捐赠的肾,那么患者真的是度日如年、很容易活不下去。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评论:如果你把自己带入一个患有恶性疾病,比如说肾衰竭患者的情况里,你不接受肾移植就活不下去了,结果你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肾脏,然后你看到对方还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换做我肯定也觉得天,太感谢了,这个人真正地救了我一命。所以这种非定向的肾脏捐赠,连医院都是非常鼓励你去宣扬的,但《纽约时报》的作者并没有提供这么一个知识背景。
钱娟:陈颀还补充说,最好不要让受捐赠的人和捐赠的人见面。捐赠器官这个事情在道德上太黑白分明了,给人的冲击太大了。比如春桃,她值不值得一个肾?她可能不值得,但我们作为社会不能做出这样的评价,不然就好像我们把一群人放在道德法庭上去审判,然后判断谁最值得接受下一个被提供的肾脏,这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每一个文明社会里都有很多条条框框去规避这些问题,在健康条件符合的情况下,尽可能保证公正让每个人都能够获得接受捐赠的机会。
但我就想到为什么不让他们见面这个事,我小时候学到过一个说法,叫“斗米恩,石米仇”,你给别人一斗米,对方会对你感恩戴德,但是你给他一石米,你们反而可能会结仇。当你得到了一个礼物,你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去回报对方时,可能感恩的心情慢慢就会变成负债感(indebtedness),而感恩(gratefulness)和负债感(indebtedness)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情感。我在听完刁刁说完这番话后,就开始想做完善事以后,人们获得的一种能力到底是什么?
Ina:《机智医生生活》里也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小孩子在惨遭车祸脑死亡之后,将器官捐献给了另一位小朋友。当时受捐赠的小朋友家里觉得,我们要给对方小朋友家里表示感谢,这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是开心的事情,但对于对方家庭来说是很难过的事情。当然,这个情况也不太一样,因为剧里是脑死亡后的捐赠,然后Dawn是活体捐赠并且是非定向捐赠。剧里解释说,之所以不告诉你器官捐赠者的名字,也可能是在很多时候,捐赠者决定捐赠的原因并不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他们也并不希望被提醒。
刁刁:回到为什么我们所有人对于这篇文章会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其实从我个人而言,我真的是把自己的很多经历,以一种非常不公平的方式投射在了Dawn的身上。因为你在社交媒体上做好事,可以瞬间获得大量的,但本质上非常空洞的好处。
钱娟:我刚刚一直在想Larson的这篇文章,她观察到了一个非常值得讨论、非常值得写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并不是有害的,她的文学创作完全是自由的。只是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她写作的动机、看到了她写作时候心里想的东西,我作为一个创作者才无法尊重她。但光看这篇文章,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Afra:刚看完这个文章的时候,我和刁刁有过一段对话,我们下意识地会想到自己在中学的时候经历霸凌或者说自己作为霸凌者的故事。其实我想聊一下,为什么这个故事会被很多人理解为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撕头花,会觉得,小圈子和小圈子之间相互攻击,是一个女性独有的问题。我还遇到一些人问,是不是只有在女作家和女作家之间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好像男性之间相互有嫌隙,不理对方就好了。我想聊一下为什么这个会变成一个看似是独有的女性间的斗争,女生打架(cat fight)。
钱娟:我也很想聊一下这个,因为我最近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world shaking)的思想转变。我认为我要开始拒绝刻薄女孩(mean girls)和女生打架的这种概念,因为它是一个自我实现式的预言。比如为什么这似乎是一个女作家之间撕头花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因为男作家之间的冲突不多,他们明明可以同样恶毒刻薄。比如说美国同时代的两个作家,戈尔·维达尔和杜鲁门·卡波特是现实生活中的敌人。有一次维达尔上电视时就形容卡波特,说他是一个堪萨斯州的家庭主妇,充满了家庭主妇才会有的这种偏见。这已经不是批评对方的写作,而是在批评对方的人格,表示这个人太low了,这样的例子其实非常多。但是往往男性之间的友谊会被升华成英雄惜英雄,男性之间的不和会变成很严肃的、值得关注的、一山不容二虎的斗争。而女性之间的友谊就很容易让人觉得是拉小团体,女性之间的不和就变成女生打架。
这是一个超越行业、超越时代,甚至超越文化背景的偏见。我们当然可以去深究它背后的很多原因,包括女性社会身份、公共身份的缺失等等。包括女性友谊这个概念在文学和电影里常年被忽略。我自己最近在深刻反思,我是不是太接受刻薄女孩(mean girls)这个概念,以及我自己成长过程中如何遭受了这个概念的影响。
Afra:其实女性斗争作为一个概念被构建出来的时候,能够非常好地解释男权世界是如何去简略女性之间的矛盾,将其简化成“意图更狭隘、格局更小,或者不具备严肃讨论可能性”的一种斗争。可是比如鲁迅和梁实秋之间才是每天在撕头花,但我们就找不到去性别化的语言去形容他们的冲突。所以我会觉得,女生打架(cat fight)这个概念能很好地去形容女性的心理和对自我、对彼此不完整的认知。
就像钱娟刚刚说的,它是一个自我实现式的预言。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在履行刻薄女孩(mean girls)的角色。我会觉得,女生之间的相互霸凌和女生之间的相互斗争是非常不光彩的,但是也是不可避免的。我甚至会非常沮丧,为什么我会被困在这样的女性斗争里面。为什么我作为班上受欢迎的人,跟男生关系特别好,就一定要去跟另一个受欢迎的女生结仇、去说对方的坏话、去试图孤立彼此。为什么我不像男生一样,惹了对方就去叫老舅给我来三个面包车的人,然后我们在校门口约个架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为什么女性的斗争要诉诸幽暗和冷暴力的方式?
钱娟: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其实你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我几乎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女生从没有被欺负过,也没有人从来没有欺负过别人。
Afra:我非常同意,这是自我折损和自我贬低,是相互的,也是一种循环。青春期的女孩子经历过这种女性斗争和在学校的霸凌之后,会再次变成一个加害者,陷入一个非常恒定的困境中,走不出来。起码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是那个样子。
刁刁:我觉得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结交,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圈子,选择自己的圈子,发现这个圈子的人都和我不一样,再走到一个新的圈子找到自我,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自然会拒绝别人,别人也会拒绝你。但刻薄女孩的概念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毒的解释方式。
钱娟: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自然现象,不是说大自然里所有有子宫的,包括人类女性都更加残忍一些,这是不对的。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因素造成了这样的情况?还是说我们正在不断地加固它,用自己的经历在为它背书?
我最近看的一本书《到家了发个消息》(Text me when you get home)的作者也试图去研究这件事情,她发现刻薄女孩其实是个很新的概念,它在几十年之内飞速地在美国文化里,以及被美国文化影响的其他文化中扎根。作者发现,近几十年来,流行文化会把年轻女孩之间的矛盾放大,而且会把它放在大荧幕上,非常深刻地刻画出来,却经常忽略女性之间的友谊。发明“刻薄女孩”的心理学家表示,一开始他发明这个概念的时候,是想帮助家长去理解他们女儿成长中所经历的事情。他给了几个标签,“刻薄女孩”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但这个标签飞速地被流行文化所接受。之后电影、电视剧,甚至音乐剧被拍出来之后,它一下就变成了似乎只有在女性身上才会出现的一种情况。
然后我小时候虽然是在中国长大,可我从来没有去质疑过“是不是女孩就是比男孩残忍”这件事情,我还会半开玩笑地去拥抱这个标签。年轻女孩的确很残忍,但男孩也可以非常残忍。我现在想起来,在初中的时候,我的一些男性朋友去排斥和他者化一些男性时做的事情是非常丑陋的,甚至还夹杂着肢体上的暴力。这是女性之间(至少在我身边)比较少见的,所以我觉得刻薄女孩是一个需要被质疑、被推翻的一个标签。
Afra:在这个事情里还有一个非常浓重的性别的元素,就是女作家这个标签。很多人在这个故事出来后,就把Larson刻画成一个心机颇深,想要上位的女作家。她成为了一个通过种种不光彩的方式去盗取别人的人生经历、盗取别人故事的存在。尤其是在中文互联网上,大家对Dawn抱有一边倒的同情,所以Larson就变成了邪恶的女作家的化身。而这样的认知,其实不太公平,过于偏颇。
一位美国科幻女作家、非常激进的女权主义者Joanna Russ在《如何抑制女性写作》(How to Suppress Women's Writing)就提过“通过蓄意地去污染你写作的意图和你写作的能动性,去诋毁女作家最初的本意,从而抑制她的自我表达”的行为。
比方说,强调Larson行为不端、出发点是坏的,把Larson刻画成一个想要上位的女作家,把严肃的文学之间的社会和种族的这些争论,偷偷摸摸地替换成了两个互相看不爽的女性拉帮结伙相互扯头花的故事,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污染写作的意图和能动性的案例。包括《纽约时报》的文章也有往女性之间的斗争的方向去引导,让我觉得这篇文章并不是“严肃的、关于种族社会道德的讨论”。
刁刁:这里有一个关于种族的点,我最不喜欢Larson的点就是她对使用种族话术的熟练程度会让你觉得她不真诚,而且这种不真诚是有害的。比如她把Dawn看成一个“Karen”(指利用白人特权牺牲他人利益来为自己获取权利的女性),并且还把这个看法写成了角色,这体现了Larson的种族视角。
Afra:我想澄清一下,我认为在Larson写“The Kindest”这篇文章的时候,她没有任何的议程(agenda),没有不好的意图。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后,Larson去维护自己的方式,是在武器化身份政治,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区分。
其实少数族裔对白人女权主义(white feminism)的态度,就是白人女性天生就不是我们的盟友。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整个英文语境下的女权主义定义,就是中产的白人女性所制定的。从一系列政策的制定、严肃的论坛讨论、到包括在学术界的讨论中,都被大量的中高产白人女性所垄断。而真正受压迫的、在链条的最底下的那群女性是不具备走上讲台,讨论女权的资格的。她们永远在白人女性写的书里,扮演那些被观察的角色。
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Against White Feminist”,翻译过来就是《对抗白人女权主义》。书里就强调这个“白人女权主义”这概念里的“白人性”(whiteness)。作者在十六七岁就被迫嫁给自己的丈夫,以取得自己在美国读书资格。她经历过家庭暴力、虐待。之后,她想办法逃离了这个家庭,自己念了法学院,然后成为了一名作家。
但是,她在步入了“中产阶级”、混入了文化圈和女权圈子后发现,当她在和所谓的主流的女权主义者讨论这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她却没有办法去告诉这帮人她经历过地狱般的虐待。因为在场的所有白人女性都享有着相似的特权和优渥的生活。于是,作者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只能对这些白人女性轻描淡写地说“我丈夫特别差劲,所以我离婚了”。然后,白人女性听众们会说:天啊我太为你高兴了——这样的回应和轻飘飘的共情,彻底消解掉了女性经历的真实的苦难。
这些操控或占据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的舆论场的人们基本上都没有真正经历过可怕的虐待,也没有经历过很多女性曾经历过的、更加需要被关注、被讨论的绝对意义上的创伤。因此她们不但是不合格的同盟,也是剥夺其他女性话语权的加害者,甚至许多白人“女性老板”(girl boss)的成功和自我吹捧式的“女性胜利”,也是基于低薪雇佣其他女性去替代她们行使育儿和家务的职责。
刁刁:对白人女权主义的批评,和现在中文互联网上对于白富美女权的批评是一样的。对这些人来说,更广大的女性苦难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然后在她们的话语体系里面,很多这种抽象的概念都会被加以利用。
钱娟:她们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而且在整个权力斗争的过程中,其实很多少数族裔、跨性别人士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在历史上,她们并没有获得这些功劳,这个功劳仿佛被白人女性占据了。以至于现在女性游行(Women's March),包括那些戴着粉色毛线帽子的女权主义者已经开始被人讽刺,因为她们并没有打算让其他那些人一起“驾驶这辆车”。
Ina:包括近来很多人谈到的文化运动——女性老板(girl boss),结果最近有好多女性CEO纷纷下台。她们大部分都是白人女性,然后爆出她们的公司对于少数族裔员工存在差别对待。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的问题,少数族裔会下意识地对白人产生不信任,甚至会觉得他们对于自己的共情都是不真诚的。这也很可能解释了为什么Larson根本不觉得Dawn是自己的朋友,而Dawn反而觉得她跟我分享了几件自己生活中的事情,那么我和这个圈子的人都是朋友,我们不只是Facebook上的朋友,我们是真正认识的、知道对方私人生活中的一件事情的朋友。
Afra:我想补充一点,因为在中文的舆论环境中,基本上90%的人都是支持Dawn的,但是在这个语境里有一层东西是缺失的:在美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当中,白人特权的存在还是如此扎眼,以至于华裔作家甚至亚裔作家一定需要抱成团,成为彼此的盟友,更进一步说,是成为战友。因为长期以来在美国的整个文学圈、文化圈子里,对世界的表述,对人内心的表述都是从白人视角出发。现在很多的伟大文学对这个世界的表述是极其不完整的,并且这种不完整没有被表述出来。
这一群亚裔作者是持续不断地,在几百年里一次又一次地被压迫、被抹去。所以我觉得在经历了这些后,这群亚裔作家的抱团、攻击白人其实是一个应激反应,因为长久以来他们遭遇了这种压迫、被白人的伪善同盟欺骗,所以才会下意识地拒绝Dawn进入他们的圈子。另一个点是,这些亚裔的同盟同时也是战友的关系,它对抗的是非常白,非常有问题的出版界。
Ina:相当于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对吧?
钱娟:对,并且是一个反应过度的防御机制。在这个具体的例子里,是非常明显的反应过度。因为Dawn是一个没有被发表的作家,结果Larson去讽刺她,说她有这个时间去游行支持捐肾,还不如多练习写作。这其实是一种打击弱者的(punch down)行为。
Afra:Dawn最倒霉的一点,就是她在Larson这些人的小圈子里被抽象成了一个白人女性(white woman),被抽象成了一个利用白人特权牺牲他人利益来为自己获取权利的女性(Karen),她被他者化了。在这个情况下,她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了。
但是,当Dawn成为了一个抽象的白人女性,又变回了一个被伤害的、具体的人之后,Larson仍在挥动身份政治的大锤去砸向Dawn。这个时候就让很多人觉得义愤填膺,把Larson看成了这个故事中的绝对反派。
回到刚刚钱娟说的,美国的出版业仍然是这么的白。如果仔细想想其中的身份政治问题,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一个成长环境相对优越的、中产的亚裔作家欺负了一个善良的穷白人,就证明“亚裔其实已经不被压迫了”。
在美国英国,如果你去看看书店书架上那些书目的结构,亚裔、少数族裔出版的书仍然只能是关于亚裔的故事。然后你再去看看商业、社科、科学的书架,你就会意识到,任何讲“大问题”的书,比如说自然、时间、意识、脑科学、宇宙等等的作家,仍然清一色全是白人。
钱娟:虽然每个人对这个故事的视角都不一样,但总的来说它还是一个能够反映我们时代精神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它不停地被讨论,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仿佛权力交替的时代,但实际上权力还是掌握在原本的那一群人手里。但会有这样的具体的、小的、激化的矛盾出现,会让你觉得我们已经翻过了这个巨大的浪潮。
刁刁:关于中文互联网上的讨论,有一点我很想纠正。Larson利用了这样的一个浪潮去纠正了一件自己做错了的事情。她的所作所为客观地伤害到了别人,而且她所创造的这种话语体系,对于捐肾的这种怀疑在客观上是有害的。但我非常不希望看到的一个词是,身份政治过度了。你看到一个人去利用女权主义来卖一些东西,你不会说女权主义过度了,你会说这是“一种对于女权主义话语体系不好的使用”。
中文互联网有人会说,我也是亚裔,我不觉得难受。但这当中存在社会的区别,他们是在一个自己的族裔作为主体的国家成长起来的。这就和美国亚裔不同了,我们之间需要大量的共情才能进行沟通。
回到这个故事本身,我觉得它归根结底是一个视角的故事,是一个视角的又一次的失控,本来Dawn书写的故事被Larson误解;这两个人的故事又被《纽约时报》重新书写。之后又被社交网络上一次又一次的书写,最后折射出的是我们每个人阴暗的或不阴暗的各个方面。
钱娟:我觉得每个人得出来的结论都不一样,对我来讲我会想我是不是太理想化了。Toni Morrison有本书对我影响特别深,她说种族主义其实就是一种他者化,当你把一个人他者化到你觉得ta不是人类的时候,你就可以对ta做一切残忍的事情。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有没有去他者化别人?甚至比如说现在人们是不是过于简单粗暴地在给白人女性贴上“利用白人特权牺牲他人利益来为自己获取权利的女性”(Karen)这个标签?我是不是应该去助长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身份政治的讨论并没有过火,反种族歧视也根本没有过火,还差得很远,但是我们也需要去纠正既定路径上的偏差。我觉得只有把这些错误纠正了,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走下去。
Afra:我的最大的收获可能是从文学上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要爱真理,不要爱那些冠冕堂皇的宇宙、爱人类、爱种族,我们要去相信、去爱、去信任一个具体的人。虽然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忽略了具体的人的话,那可能就是暴行,那可能就是残忍。
责任编辑:龚思量
校对:徐亦嘉
原地址:https://chinesefood8.com/27989.html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