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大凡作为子女的,都曾有过追忆父母,并将其往事记录下来的愿望,可屡屡因无从入手,终不能如愿,我也不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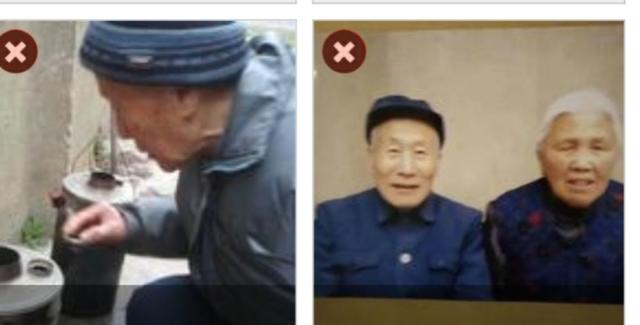
2010年左右(晚年的父母)
最近,在朋友圈偶遇影响颇广的《原野牧歌》,发现她推送的作品,不乏追忆父辈之佳作。受此启发,随萌发尝试来写一写的想法。于是,便打开多年不用了的电脑,敲起了不够熟练了的键盘。此时此刻方悟“书到用时方很少”。回眸过去的苦难岁月,为的是要珍惜当下,更是为了未来。父辈们为我们带来了,今天这么美好的生活,夯实了这样坚实的基础,我辈岂能止步,后来者能躺否?

帆船江上行
父亲于2015.1.24离开了这个世界。唯,让他不放心的是,从五六个月大,就被他和我母亲亲手带大,看着上大学并独自找到了工作的外孙女金,工作后尚未成家。但,他立马又说,也不错,能在城市大医院当个护士也挺好的。

2021年初夏笔者外甥女单位医护人员运动会留影
父亲离开我们已近七年了。父,为家族艰辛打拼的点点滴滴,仍历历在目。父亲出生在民不聊生的战乱时代。少年时,目睹了日本兵抢夺百姓财物的汹狠,感受过解放大军,渡江下江南场面之壮阔。成年后,亲历了五四年发大水,江水漫灌家园之苦,体验了共产风,饿死自己的父亲和三岁娇女的切肤之痛,历经了文革社会之躁动,为改革开放鼓个掌,享受过家国日新月异变化之甜蜜。
其职业虽说是农民,但却干了很多不是一般农民都能干的活。木工、瓦工、补修工(补鞋、补锅、补塑料盆、补雨伞等)。这些活,他都干过,并做的很好。记得2005年以后,妻做蒸饭近十年,木盒坏了不知多少次。都是他给救急帮忙,致使一天没影响学生早餐的供应。特忙时节,他不分天晴天阴或风雨,或冰雪,一年四季来给我们照看店面帮帮收银。
改革开放后,家里还开过小店,兼送货下乡,变成了名符其实的“送货郎”。再后来,直到他晚年,只要他还能动,仍然坚持在加工制作小农具——打蒜苔的梭刀。至今,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其操作流程和相关技术要领。采购符合规格的金属板材,然后切割成单个刀片(长方形),继而切角、锤平、凿小窝、磨砂,打光、除锈、焊接、冲眼、安把等诸多手脚。他充分利用当时有限的土地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种植过扎扫帚用的地肤草,并自己加工,自己销售。其产品除了本地的洲上洲外泥汊、白茆、汤沟等地,还多年远销南京的江心洲、八卦洲和柳州等种植大蒜的产地。因为哪些从黑沙洲迁移至南京的乡村他认准了父亲制作的产品,价廉,质优,用的放心。父亲虽不能称作大国工匠,但至少,也该能称作民间艺人了。这都得益于他的吃苦耐劳,不断进取,善于学习,乐于钻研的精神。在其生活的八十一年的风风雨雨中,历尽磨难,也曾历经多次生死考验,有诸多可歌可泣可书之处。
下面要写的是,建国之初,我的父母在即将开始属于他们的新生活时,发生的一次惊心动魄的事件。兼将此事发生前后,也是他们往后近六十载共同生活前后近八十多年间,父辈们所历经的风风雨雨劳作与生活的片段,撷取一二记之,以示崇敬。

改革开放之初父母与子女合影
1957年5月1日,农历丁酉鸡年四月初二日。白马洲(今白茆)沿江一带刮起了五到六级东北风,江面阵风七到八级。俗话说:长江无风三尺浪。遇到这样的天气,江面已经浪白了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父,早早地请来了本队邻里,两位德高望众的长者。一位是范世顺(现白茆三垅村干周宜武外公),善于表达,讲话幽默风趣,很受地方邻里尊敬。因其只有一只眼睛可视,人称瞎大爷;另一位尊敬的长者是李大先生家老伴,人称李大师娘(现无为一中,原六洲中学思政室主任李大强的奶奶)。他们冒着雨,顶着风,搭乘着从本大队周宗兵家专门请来的一条打鱼船,由黑沙洲中心的小北岛出发,向当年日本兵在此建过兵营的“鬼子窝”,即现在的神塘河上、泥汊下的方向蛇行行进。住在江边的人大抵都知道,因风向,此船不可能像如今,只要机器马达一响,船头径直朝北,即能快速抵达江对岸,到达我母亲的娘家所在地三垅。其实,过去这两地也就是一江之隔。如果遇风平浪静,睛光妖娆时节,两岸鸡犬相闻。那年月,几乎所有的船只航行,只能借助人力或自然风。无风时,只能靠人背,纤夫名由此而来。也就是,用数个人肩挎着纤绳,勾着腰,低头用力向前。前面第一人,头可能要抬高一点,以便看行进路线,后面的则只要看到前人的脚后跟即可。纤夫只需要将船背至想抵达的目的地上游对岸,然后将船头旋转大约四十五度朝对江,借助江水自然流动和船上桨橹的帮助,逐渐驶向目标。至于旋转朝左还是朝右视你是从哪去哪而定。这种情况一直沿续到上个世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那时的江面仍可见白帆点点,可以听到不绝于耳的樯橹声。

当年的船工劳作画面
那日,刮的是东北风,由南向北属顶风行驶。于是,只可采取“由曲达直”的蛇行前进策略——这也是江边渔人或船工千百年来智慧与经验的积累。用今天的流体力学知识不难理解这其中的原理和奥秘。这船在风雨中歪着身子破浪前行,船体倾角或大或小,角度不停地变化着。时儿四十度角,时儿五十度角……。船桅上打了许多补丁的帆,有多处被风扯碎,在风中不停地摆动,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借助风力,小船在摇晃中前行至江心处。此时,浪如山头。小船在波峰与波谷之间时隐时现。如果此时你站在岸边眺望,怕也只能看到模模糊糊的桅杆顶端的一小截(无为方言,一小段的意思),恰似在江水中搅拌着什么东西似的,在不停地移动着。江两岸及船上的人,无不期待着船只早早靠岸。终于离北岸越来越近了。100米,50米,30米,此时船上的人们,悬着的一颗心稍稍平复了些。可是突然,船工发现,岸边“江坑子”壁陡成崖,无法上岸。船只只好向坡缓的下游顶着风去寻找着陆点。可是,就在船离岸约摸二十来米处,浪花更大了。原来,卷向北岸边的浪被岸边“江坑子”(陡峭岸线的俗称)狠狠地推挡了回来,挡回的浪像是受了委屈似的,赌着气扑向南边,与其后跟进来的浪相汇合,两股浪叠加撕扯在了一起,很快便形成了更大的峰峦。终于,这只不算太小的木船,驾不住巨浪的蹂躏——迎亲船翻了,翻了个底朝天。
船是请来帮忙接亲的,虽上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从七邻八舍里凑借来的七八把雨伞,还有船仓中供人行走的铺板,以及平时捕鱼用的一些工具等,胡乱地极不情愿似的散落在水面,漂浮在江中,随波逐流,或沉去,或漂浮,渐渐流向了下游,或上或下。有几块,向着下游随流水,迎着浪花扑过去,好像是在为他的主人在泄愤鸣屈似的,并渐渐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生命止上,人命关天。诚如一切自然灾害一样,在这种突然到来的事件面前,第一步还是靠自救。虽瞎大爷只有一只好眼睛,但他还是靠着心智,本能地用手一把抓住了李大师娘衣服,另一只手抓住了一只漂浮在水面的木桨,利用双脚上下扑打着向岸边游去。
船老大因多年在江上捕鱼打拼,其能力自不便说。
好在我外公不放心今天的天气,一行人早就在江边候着,目睹此景,会水的人们,便奋不顾身跳入江水中,开展营救。四月初的天气,虽非冬季,但江水仍带有寒意。况且,船上落水的这几位,当年并不是姑娘小伙,可都是上了岁数的人。湿衣、湿裤缠在身上很是难受。时间一久,就会瑟瑟发抖。落水者上岸后,我的外公对他们进行了妥善的处置。随后,便换乘坐上了,由我外公安排的代家渡船,送我母亲及一行人向洲上行进。当年,代家渡口位于代家大窝,在季家渡口之下,位于今天的白茆江坝上游的垅凝与三垅搭界处。因代家船主是我外公的表哥,其船吨位比来时那条船只大,超十吨以上,加上是顺风行,外公很是放心。果不其然,船很快平安地将我母亲及一行人送抵洲上。我外公周隆盛(又周隆胜)是读了几天私塾的。少年时代就显得不一般,办事干练、持重。方圆数十里,乡里乡亲、亲朋好友等家中,但凡遇难解困惑之事,便会想到他老人家。尤如老郎中给伤风感冒患者问诊把脉般,手到病除。因此,人称“诸葛先生”。关于这情况,在我十六七岁上师范与他聊天时就已感受到。他能脱口而出《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全篇,讲一些当时诸多我未知的知识,令我瞠目结舌,钦佩直至。
母亲,周义珍(周宜珍),1938年10月13日(戊寅虎年八月二十)出生,在家中兄弟姐妹当中排行老二,时年十九岁。

1963冬日前后笔者被母亲抱在怀中
父亲张明道,1934年9月18日(甲戊狗年八月初十)出生,时年二十三岁。当年,我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是土改时,政府给张氏一门划成份为“雇农”的主要依据,即比贫农还差、还苦的人家,无一点土地,专靠帮人家干活。父亲二十一岁娶过一门亲,本队邻里李家姑娘,人称“小姑娘"。母亲告诉我,小时她舅父在三垅(项传万之父)。小时曾抱给三垅冯家做童养媳,长大后想家,整天哭闹,不从。于是又返回洲上的家中。后嫁给我父,一年不到,病故。母亲跟我谈心时说过,“小姑娘”从小与母亲经常在一起玩耍,因冯家与母亲家住在一块地上,为邻里。其实,他们也是远房老表关系。“小姑娘”的外公与我母亲的外公项修成一个辈份(《渡江侦察记一一为了不能忘却的小木盆》故事中提及过)。至于为什么人们一直称她小姑娘,那是因为过去的女人没有名字。母亲说,起名是后来参加生产队劳动记工分需要,才开始有的事了。再后来,女人开始可以念书了,起名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自不便说。
1954年梅雨时节,长江中游有1800 公里流域遭遇百年未遇的特大自然灾害。仅长江安徽华阳河地区分洪,无为大堤溃决,决口分洪量达87亿六方米,淹没耕地34.3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达290万。整个长江流域,中段五省受灾人口1888万人,死亡3.3万人,京广铁路不能正常通车达100天,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时值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抗美援朝结束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可想而知,我们的党和我们人民是多么不易啊!真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呵!当年,你若站在大磕山朝北一望,一片汪洋,无边无际,一浪白。这一年的冬天,天气十分寒冷。父亲到严桥红庙老家(祖籍地)取粮食,因为张家一门有不少张嘴要吃要喝。老大、老二两家家眷都在洲上等着粮食,无米下锅。此时,父亲大哥张明荣在无为红庙老家帮人家织布谋生,二哥张明仙懂点篾器活手艺,也在帮人家修补竹器谋生。父亲光脚穿着草鞋,没吃没喝的从冰上来回走了近一百五十里路。父亲与母亲组成家庭时,我的爷爷奶奶还带着我的小叔明开,仍在新港那边的大磕山山头上,并没有回洲上。原来,五四年发大水,政府将洲上老弱病残零时迁移安置到了江南新港的大磕山和小磕山上避难。
几日前,父亲还挑着工具挑子,一头是工具箱,里面装着斧、锯、刨,凿、锤等;另一头是一条“懒板凳”加上给木盆、木桶、“腰子盆”、“大扎盆”等修理时要用到的材料,如给各种桶、盆打箍用的竹篾、竹削子(后期发展变成枣核钉)。父亲那时刚二十出头,在新港大磕山和小磕山这两个山头间的一个卧棚一个卧棚的灾民点住户间,穿棱行走,十分疲乏。因这样的劳作方式,从无为大堤决口到现在,已差不多接近三年了。但为了这个家,他艰难地支撑着,默默无闻。
前述所谓的卧棚,即找几根竹木支撑成人字形,再在其上披上杂草树枝,当时可没有铁皮和塑料制品可用,只能就地取材,一切依靠大自然。
父亲是在1954年春节期间来无为观震潮边(现绣溪公园北,老无为一中南大门东)的郭木匠郭老爹家学木匠活。如电视中所描述的一样,什么活都干,帮洗衣,带孩子,烧水做饭,倒马桶等等。后因堤溃圩破只做了半年的学徒,便终止了求学路。尽管这样,父亲后来回忆时还很惋惜,觉得学徒生涯太短暂了。回家后,用人家“捡精”废弃的棺材板练习制作木门、“猪食盆”(喂猪食用的木盆)等来练手。这不仅练了手,同时也为家庭争点“花销钱”(零花钱)。过去很多人家的大门都是由这种方式获得的,民间改说为“棺材”即既升“官”又能发大“财”。其实,那是一种无奈之举。当年科技不发达,物资匮乏,是没办法的办法。就这样,越练越精,也就是靠着他的这门子手艺,应了急。帮助父母、四弟、五弟,抑或在山头的侄儿士银、侄女等张氏后代渡过了荒年的一个又一个难关。因为此时,侄女、侄子他们的父亲在外串乡讨活口。古话说的好“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父亲的特长是木工活中的“圆木”,在“方木”方面则显得稍差一些,但凑合着也行。但他这一专业不足,在大灾之年,水患之时并不影响的他的营生。灾民正需要他的“圆木”技能。修修补补大都为“圆木”活。“圆木”属木工中高精尖技术,因为圆木是农家生活用具中盛水器物俱多,一点不能含糊。
从1954年破圩之后,从洲上临时搬去逃荒的人,至今仍有很多老老小小没有返回洲上,仍生活在山头。这么长的时间,难免有需要修理的日常生活用具。诸如烧饭的锅盖、盛水木桶、洗脸洗脚有时共用的木盆等。那时,哪有什么钱,象征性给一点吃的东西,什么都有,五花八门。当时,救灾粮的分配是有严格规定的,按每家每户,按人头,分男女,分老少,有区别差异化的配给。因此,粮食甚为珍贵。当然,也有实在没的东西可给的人家,我父也照样给予修理。尤如当年一句民谣说的那样“巴根草根连着根,天下穷人心连心”。在党的领导下,互助、自救相结合,战天斗地,共克时艰。
这几日父亲显得格的忙,因为他要在迎娶我母亲之前凑齐我爷爷奶奶他们的一段时日的口粮。他安顿好我的爷爷奶奶,还有一位五六岁的弟弟明开。在父亲准备乘船返回洲上时,一位曾得到父亲救助过的老乡,听奶奶说父亲近日要回洲上成亲,便将一只约2斤多重的母鸡给了奶奶,说是用得着。父亲便在那年四月初二之前开了路条,当年搭渡船往来人员需开据相关证明,俗称路条。
他如期返回了洲上。两间特殊材料造的房子是由他自己一手所为。它是由葵花杆子立在地上糊泥成墙,小麦杆子盖的天棚。类似一个长方体,再从一方下披了一小间,只在一侧开了一个门。因形似马的屁股,母亲一直称此屋为“马屁股屋”。当我第一次听到时,不觉十分的好奇。我想,我跑了不少地方,见过不少建筑,还是第一次听说,还有一种房子叫“马屁股屋”的。我费劲地想,终于明白,从侧面看解放牌汔车车厢加上驾驶室,可比拟之。此房业已多年失修,外墙面在雨水的冲洗下已斑驳陆离。遇风雨日,则上漏下湿,泥泞一地。室内除了晚上休息用的一张苦楝树打的,已使用多年的旧床,正静静等待她新主人的到来。灶台上,一只豁了口的盐钵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实在没什么东西,因此它显得十分的耀眼。这钵还是因为儿子要重新结婚成家,为父为母的将他们使用了多年的物件给了他的儿子。我的母亲后来说,这是一件传家宝。言外之意,母亲深知我爷爷奶奶他们的艰难。其实,这只是一件十分普通的泥陶,涂了一层蓝色的釉而已。直到2003年夏,我将父母接到我身边白茆镇上居住时,此物件才光荣退休。母亲后来回忆:那天晚上没有什么客人,只有一直在为父亲张罗的“小姑娘"的母亲,还有惊魂末定的两位“迎亲”老人。晚饭十分的寒酸一一仅一只头天晚上不知咋死了的,从大磕山带回的那只鸡,打理清洗后烧制成了一道菜,再配了两个蔬菜,就此而过。
第二天,我母亲从父亲口中获知,这床上的被子和蚊帐都是父亲临时借来的。没过两天便又送还给了人家。今天的人们肯定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但我深信不疑。不是因为是母亲讲的话可信,而是在我上初中时,我同样见证过同样的一幕。
一提蚊帐,我便想到父亲在我十二、三岁时,托门口当年在四川当兵的世荣二舅,代购了麻布帐子,以备儿子将来结婚时用。四川麻布是当时中国的品牌。
时间大概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刚上初中。不久,本生产队章启山二儿子章金庐,好不容易经人介绍谈了一个女朋友,可因家贫,结婚时没有蚊帐。父亲若有所思的回到家,便将这件为儿子准备的结婚用品拿了出来,借给了人家救急。当时,母亲很不理解。因为这是为自己孩子将来准备的结婚用品,怎么能随随便便借给人家用呢?按中国传统习俗,结婚之人,称作新人。新人用品也一律用新的,主要是图彩头,图吉利。
母亲按传统规矩来说此事,一点没有错。可父亲这么做,也有他的道理。可现在仔细想想就不难理解他了。他所做的这一切——其一是怕儿子重蹈覆辙,步父后尘,早备蚊帐;其二是同病相怜,同情和自己当年一样的邻里乡亲。他那时哪里知道,这些物品后来全部淘汰。

2020年芜湖三桥暨商合杭高铁过江大桥通车前市政府专车安排市民免费参观我和毌亲留影
国家发展的速度让人不敢相信。而在之后的生活中,父亲为子女,为家庭生计,在自己的人生中多次遇险,险象环生。一次是,冬日里,为防冷,在大棚里焊梭刀,火烙铁需煤炭炉加热,空气不流通,时间一久,煤气集聚,引发中毒。口吐白沫,人事不知,险些丢命。歪打正着,幸亏母亲喊人将其抬到棚外,置于家中门口。当年,我父母住在江堤之上的三间土墙瓦房内。堤上空气流动快,终于死里逃生。试想,若一会移出棚中,其结果就是另一种情况了。另一次是家中开小店乘船进货,风雨夜,船行至三江口时,“马达”坏了,船像一片树叶随波逐流。新港、黑沙洲、白茆南垅三处江水汇聚在一处,浪高水急。此处是长江芜湖至荻港段,水上交通最险的地方,好似陆地上丁字形路口。那夜,船险些被撞沉。父亲回忆说,就在即将被撞上时,他急中生智,将拖把攒上柴油,好不容易将火点着示警,又逃了一难;再一次就是“共产风”时,逃难至江西,放竹排途中刮台风,排撞崖壁,命悬一线。父亲常说,我算幸运了。多次从阎王爷门口侧肩过。共产风时,饥饿晕倒,躺在床上都爬不起来。双腿浮肿,面黄肌瘦。此刻,他的父亲,我的爷爷已经饿死。另,五八年出生,时已三岁的女儿在我母亲的怀中,静静地走了。当时只剩下皮包骨头。母亲后来回忆说,张青天(指张凯帆)一日来家乡无为,打开粮仓放粮,父亲得救了。我这未曾谋面的姐姐,也渐渐脸色好了起来。母亲继续说道,我认为已经不要紧了,不得死了。可没过几日,风声又紧了,从大食堂打回来的饭,哪有米,只有清水上漂了几片麦麸。那时大人靠野菜、树叶充饥。可怜三岁的孩子哪能撑得住。姐姐1958年8月生人,若在世,也已经64岁了。
相对父亲,母亲的生活则显得平平淡淡些。这可能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所致。

2018年夏母亲在西安机场
母亲和父亲一样十分的勤劳节俭。他除了忙里,还要忙外——在生产队做工挣点工分,好年终分的红。但,扣除平时分得的粮食及柴草之类,诸如分得季节性瓜果杂粮,或塘口起鱼分得一条鳊鱼、两个小鳙鱼,一梱花生杆子,两堆柴草,等等。在剔除人囗所占成头,略有微薄所得。为了将当年漂走的雨伞赔偿给人家,父母节衣缩食。那年月家中有把伞也是一种奢侈。

2014年清明时节,父亲在自家院子(外孙女摄)
母亲是一位非常能吃得苦的人,别人家早晚餐同样是两个红薯,可能还要添加一碗小菜或烧一碟青菜、辣椒什么的。而我的母亲早晚餐时,则非常的随意,就只是一两个红薯,有时连口开水都舍不得烧。至今,她这种生活理念仍延续保持着。不要浪费,不能浪费。父辈们用他们历经的苦难在时时提醒着我与你们,乃至薪火相传的子子孙孙们。这是一种无言的忠告。

2021年春妻陪孙女在芜湖白茆江坝至黑沙洲渡口
母亲是一位极富善心,好善乐施的人。时间大约在1959年年底,一日,天刚“擦黑”。母亲到塘中取水时,发现一人躺在水塘边,已淹淹一息。母亲放下手中的水桶,轻轻地呼唤着她,她终于苏醒了。后得知,她乘船刚从对面过江而来,欲回球场,即如今的新球村的娘家去,其父亲姓王(后因崩江其弟搬迁泥汊幸福洲)。刚才,是因为实在饿得受不了,去塘中取点水喝充饥,没想到晕倒了。母亲随后将其扶到我家床上,让其躺着。随即从一隐蔽处拿了好几个山芋在锅中烀了起来。烀好后,先捡了两个。她很快就吃掉了。母亲又取了三个让其吃,她抬起了头,看了看母亲,似乎想吃但又觉得不妥。因为粮食在当时太稀缺了。母亲懂她的意思,说道“没有关系的”。并告诉他,我家男人(指我父)在外帮人家“送报功”修东西,人家给了些粮食,还有一些。接着,她一口气吃掉了五个山芋。虽不大,但也不算小。她向母亲跪下了,当她知道我父在家排行老三时,便称母亲“三姨娘"(按她孩子称呼我妈)。母亲随后留她在我家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便送她上路回球场的娘家。共产风那些年月,大埂上的路两侧,长满了一人多高的杂草,因已年关,草木枯黄,所以母亲没敢让其一人连夜赶路。毕竞,从中心到球场足有七八里。其一路在埂旁,有好几个墓地。埋着因饥致死的人们。当时,埂上住的人家少,十分孤单。
华夏民族夙有“点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传统。果不其然,第二年夏收季节,糯稻收割结束时节,家里突然来了一位与母亲年纪相仿者。背着一个布袋,装了约5斤糯米和手工缝制的一套小花布衣服。原来去年她在我家时,知道了我有一个姐姐,当时2岁多一点。此行她是从当时隶属泥汊人民公社民主大队专程来感恩的。她和毌亲一样纯朴墩厚,五十年前,她大约三十多岁,宽脸,大眼,一副富贵相,但记得她听力不够好。其老公名曰徐家政(又徐家正),我还隐约记得些。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曾乘小轮,由当时黑沙洲水口轮船码头出发,到泥汊下船。后沿无为大堤走到获港板子矶对面,江堤上有一堆鹅卵石处,再沿右手下堤,步行约二十分钟即可到达她家。当时,她家四周都是塘囗。我清楚记得,她有一个女儿,如今怕已快七十了,一个儿子后来成了我二伯父的女婿,名叫徐向东。她的大女儿,比我1960年饿死的姐相稍大些。底下有好几个儿子,长得都挺壮实。隐约有一个小名叫"二呆瓜子”的与我一般大。曾记得有一年过年到他家,雨雪天,我小叔受我父指派,由我领路挑了一担米送给老干爹家。老干爹激动万分,孩子多,虽种稻,但上缴后。余粮不够吃。时值青黄不接,此乃雪中送炭。当时,我见“二呆瓜子"踩着自制的"高脚"串门子,那时买不起胶鞋。当年,父亲看中了他家子女成群,便将我这个唯一的儿子接给他家,农村人称作"干儿子"并随了他家姓氏,取名玉,示珍贵。因其徐家儿子辈分为“太"字,故将我原名“张士和”改为如今这号。
工作后,有意欲改回之愿,但考虑到不太客易,且姓名本就是一个符号,不改也罢。如今老干娘的亲侄已成了共和国税务部门的一位高干,位居国家税务总局要职。其家乡黑沙洲人民,以及上过无为师范的人们都为之感到骄傲。

黑沙洲如今包括老洲天然洲,靠白茆这侧有一三包子
黑沙洲,是当年父辈们迁徙来此拓荒开垦的落脚点,在这里他们将青春奉献,将汗水洒遍;这里也是他们和作为子女的我们这些后人走出打拼的起点。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岁月如烟,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那些尘封了的往事,随着祖国日益强大,人民生活的日益富裕,也渐渐地在人们的脑海中越发地糢糊起来,若真,若梦。

1993年父母与子女及孙子孙女们全家福
但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永远牢记来时路,以便能行稳致远。谨记,为念,为盼。
原地址:https://chinesefood8.com/4240.html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