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稿 / 张梦新
张梦新,1948年2月出生于浙江富阳大源镇岭下张村。曾任杭州大学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新闻系党总支书记、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后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奶奶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却经历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深秋,细雨绵绵,我又去了一趟那座魂牵梦萦的小山村。一路上我都在想我的奶奶。村口、溪边、山间小路、大树脚下,仿佛到处都还能看到奶奶的身影。
奶奶离开已经46年了,可我总觉得昨天她还跟我们在一起,她的音容笑貌总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奶奶生于1879年,历经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1973年10月27日以95岁高龄谢世。到今年,奶奶正好阴寿140岁。
01 敬胡公虔诚礼拜,修石桥喜得贵子我奶奶楼氏,讳金珠,生于清光绪五年农历五月初八(公历1879年6月27日)。及笄之年,嫁到了富阳大源镇的岭下张村。
这是个偏远贫穷的小山村,坐落在毗邻萧山云石乡的小黄岭下。整个村子依山溪而建,解放初才四百来口人。当地有首民谣:
山里山,
湾里湾,
十八乘竹桥到岭下。
天空只有笠帽大,
溪坑只有榼漏大。
地无三尺平,
人无三分銀,
十里不听稻桶响。
民谣形象地道出了小山村山路崎岖、无田无稻的贫穷面貌。
但是老天爷是仁慈的,岭下张村四周漫山遍野长满了青青翠竹。山里人靠山吃山,或是砍下青竹浸料做土纸,或是做篾匠,编篮织筐,或是砍下毛竹换钱。
据《富春张氏宗谱》,岭下张氏的祖先是明朝嘉靖年间来自萧山衡河的彬二公。为避战乱,彬二公携家小来到这穷乡僻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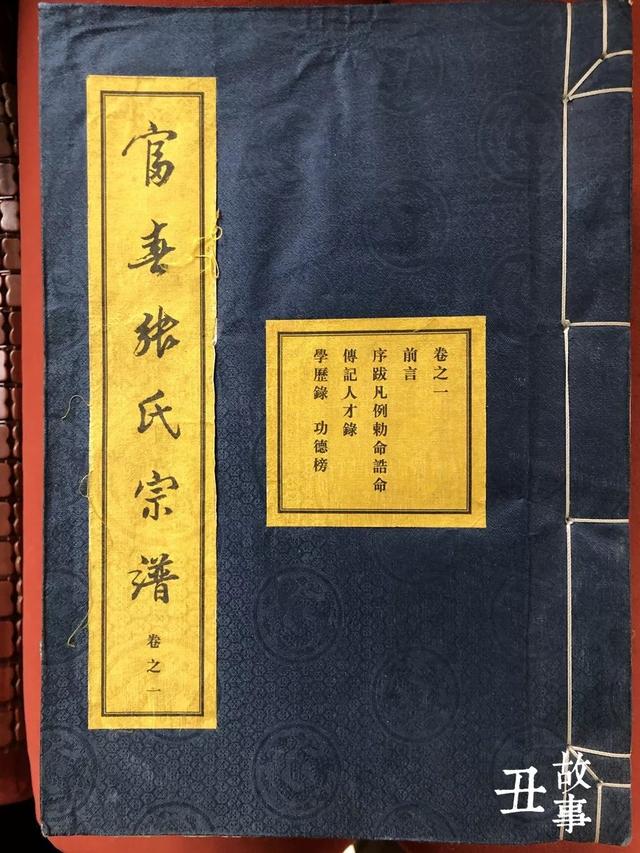
富春张氏宗谱
四百年来,彬二公的子孙后代繁衍成了一个村落。除了嫁进来的女人,全村人都姓张,同根同源。
我爷爷讳元悦,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农历九月初三,比我奶奶年长11岁。
他是干活的一把好手,非常勤快。曾听奶奶说,我爷爷身强力壮,每天天蒙蒙亮就上山砍毛竹斫柴,等其他农户吃完早饭出门干活时,他已经从山上背回两趟毛竹或柴火了。
奶奶和爷爷婚后琴瑟和谐,先后生了六个孩子,居然全是女孩。在清末民初,老百姓还是很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于是爷爷又从诸暨沙溪王家娶了我二奶奶。
二奶奶王氏比我奶奶正好小一肖,也是属兔的,但是婚后一年,二奶奶的肚子仍不见动静。
村头有座胡公庙,供奉的是胡公菩萨。
当然我以后知道了,胡公庙供奉的是宋代清官胡则。胡则为官清廉,为民请命减免赋税,又抵御外侮,因而深受民众爱戴,在其家乡浙江永康和杭州、金华、富阳、萧山一带,百姓都建有胡公庙祭祀他。

几经修葺的胡公庙
1959年8月,毛泽东主席的专列由庐山返京途经金华,接见部分地方领导时说:“永康不是有方岩山吗?方岩山上有个吴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
我奶奶信佛,于是拉着爷爷去胡公庙上香。胡公庙建在山溪的对岸,没有桥,善男信女进香要绕很大一圈。
为了表示对胡公的敬仰,爷爷奶奶出资购买了一批石料,雇人在胡公庙前修了一座石桥,方便人们过溪干活和前往胡公庙进香。
修座石桥对富贵人家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我爷爷奶奶这样的穷人来说,可是一大笔开支。
下大雨时会有山洪,所以造桥也很是不易。爷爷奶奶硬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造成了一座漂亮的石拱桥。从此村民们到溪对岸干活,或者去胡公庙烧香,都变得很方便了。
说也奇怪,修造石桥后,两个奶奶先后怀了孕。小奶奶于民国八年(1919)正月十六生下一子,即我大伯正祥;我奶奶于民国九年(1920)正月初八生了我父亲麟祥;同年十月二十日,小奶奶又生下我小伯芝祥。
当年我奶奶41岁,在那个年代绝对称得上高龄产妇。
02 遭变故力挽狂澜 葬夫君嫁女育儿两年时间连得三子,爷爷奶奶真是喜出望外。
但是一家十多口人的住房矛盾也随之更显突出。为了解决全家的安居问题,爷爷决定建造新屋。
岭下张村平地甚少,一条山溪由北而南流贯全村,溪坑两边的房子鳞次栉比,几无空隙。

岭下张村
爷爷选择到村北的鸦雀窠造房。这是当年全村地势最高之处,顾名思义,“鸦雀窠”就是老鸦、鹰雀做窝的地方。
爷爷选中的房基地紧挨山崖,需要挖掉大片岩石。往往忙活一个白天挖出一块平地,晚上山体滑落,石头泥块又覆盖了刚挖出的房基地。
就这样挖了塌,塌了挖,爷爷奶奶毫不气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奋斗不止。
奶奶虽是小脚(那可是真正的三寸金莲),但也手提肩挑,烧水送饭到工地。
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一块平整的宅基地终于被清理出来。
又历经寒暑,垒石砌砖,立柱筑墙,上梁盖瓦,一幢三间二弄、总面积达280余平方的两层楼房终于拔地而起。

“鸦雀窠”
新房子北近“将军帽”(此山因山头似一武将的头盔,故村民称之),东对小黄岭,西枕青山,南临碧溪,黛瓦白墙,美轮美奂,风景独好。
可能是又要造房子又要忙农活,过度的劳累透支了爷爷的精力,他病倒了。
旧中国的农村原就缺医少药,岭下张村地处穷乡僻壤,农民们大都没文化。据奶奶说,爷爷是因为本应服用止泻的药而误服了导泻的药,病情突然加剧恶化,又得不到及时抢救,竟于民国十一年(1922)七月廿八日子时溘然离世,享年仅五十四岁。
爷爷的突然去世犹如晴天霹雳,使得原先幸福美满的日子骤然变得充满悲凉,两位奶奶更是悲痛欲绝。
当时我奶奶四十出头,二奶奶刚三十岁,九个孩子中最大的不足二十,我大伯三岁,我父亲二岁,小伯才一岁多。这样一种家庭状况,任谁也都要叫皇天。
在这突遭变故的危难时刻,奶奶显示了她刚毅坚强的本色,挺身而出,主政持家。
她首先操办了我爷爷的葬礼,在亲友们的帮助下,带领家人把爷爷安葬在村南头的琴坞山脚。
前几年,我曾在堂妹夫张海校的陪同下,前往爷爷坟头祭奠。爷爷的坟在琴坞山,西向而立——那正是我家祖屋的方向。奶奶希望爷爷在天之灵能望到家人和他的儿女们,并庇佑他们。
同时,奶奶又请人打理家里的竹山并耕种山地,以解决一家人的生计。
就这样,奶奶以柔弱之躯挽狂澜于既倒,成了张家名副其实的当家人和顶梁柱。
奶奶先后操办了几个长成的女儿出嫁,据《富春张氏宗谱》记载:“长适萧山尖山下姜关金,次适姚村章月大,三适史家山楼伯顺,幼适萧山斜爿坞俞阿祥。”
奶奶自己不识字,但她从爷爷的猝死深深感受到文化的重要性。她让我大伯、父亲和小伯三兄弟都在村小读书认字。
听我父亲说过,当时家里很穷,书根本读不起。好在村里人都是彬二公的后裔,而彬二公又是私塾先生出身,所以村里颇有耕读传家之风,而且相处和睦,互相帮助。
村小的教书先生见我奶奶孤儿寡母拉扯几个孩子很不易,就允许我父亲他们哥仨跟着其他孩子一起读书,没有收他们一分钱,甚至连他们的课本还是教书先生送的。

年轻时的父亲
也许冥冥之中祖宗庇佑,抑或是受到慈母的鞭策和鼓励,我幼小失怙的父亲学习很有天分,他读书悟性高,记忆力强,不怕吃苦,又很用功,所以很快在小伙伴中脱颖而出。
村小的先生也爱才惜才,主动找到我奶奶,说麟祥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让我奶奶好好培养他读书。于是我奶奶毅然卖掉了山上的许多毛竹,又求亲靠友借来了学费,让我父亲到杭州太庙巷小学(即现在的紫阳小学)读书。
我父亲深知到省城杭州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因此非常珍惜,学习特别用功。不但高小顺利毕业,而且再接再厉,考上了萧山的湘湖师范。
湘湖师范创办于1928年,最初叫浙江省立乡村师范学校,后于1933年改名为浙江省湘湖乡村师范学校,1957年定名为浙江省湘湖师范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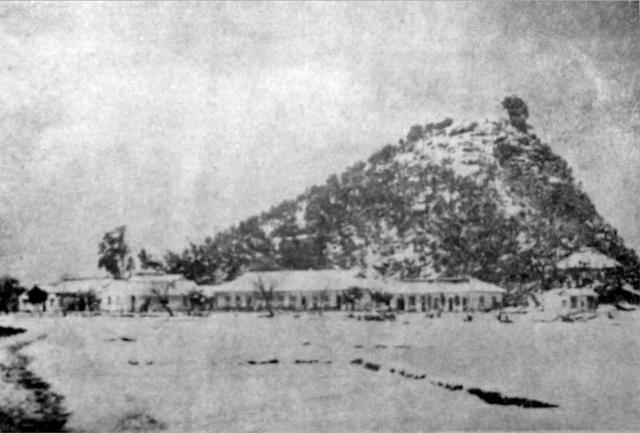
湘湖师范学校雪景
由于是经省教育厅批准的省立师范,当时湘湖师范学生的膳食费用是省政府拨款的。我父亲家庭贫困,能就读湘湖师范已是他最好的选择。
更幸运的是,他不但读了个好学校,还遇到了许多好老师。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高足金海观先生于1932年出任湘湖师范的第六任校长。他主政湘师的25年里,很好地践行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注重生活教育、生产教育、科学教育和社会教育,四方招纳贤才名师来湘湖任教。
金海观校长是诸暨人,与他同邑的俞公达先生二十年代末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此前担任过诸暨县教育局局长和松江县立师范的教导主任,为人正直,办事公道,金校长就聘请俞公达先生担任学校的生活指导部主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日军飞机轰炸上海、杭州等城市。为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中国的许多高等院校纷纷西迁。
当年11月,浙江大学、湘湖师范等校都开始迁往浙西南山区,湘湖师范在金海观校长的带领下西迁到了丽水松阳,俞公达先生担任了湘师古市分部的主任。
当时还在湘师读书的我父亲跟着湘湖师范的西迁师生一起到了松阳。

湘湖师范全体师生在松阳市合影
“梅花香自苦寒来”,我父亲来自富阳的小山村,深知读书的来之不易,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学习,成绩也比较好。这个眼睛明亮、五官清秀的年青学生引起了俞公达先生的关注。
作为湘师古市分部的主任,他查阅到了我父亲的相关材料,有意地找我父亲谈话。通过多次交流,俞公达先生渐渐了解了这位学生,同样出身贫苦农家,同样想通过勤学苦读改变命运(公达先生也是先考上杭州第一师范,再考上上海大夏大学的),又同样为人正直善良。
俞公达先生喜欢上了我父亲,并把自己正在湘湖师范读书的胞妹俞纯琏介绍给了他。我父亲比俞纯琏高两届,两位年轻人由相识、相知到相爱。

1940年,父亲从湘湖师范毕业,母亲送给父亲照片留念
1940年和1942年,他们先后从湘湖师范毕业。1943年,两人举行了婚礼。
1939年,浙江大学在丽水龙泉创办了浙大龙泉分校,我父亲经过努力,于1941年考上了浙大龙泉分校师范学院的国文系,成了岭下张村第一个,也是解放前唯一的大学生。我舅舅俞公达,则是他家乡诸暨次坞文水塘村的第一个大学生。
喜讯传到富阳老家,众乡亲齐相庆贺,我年过花甲的奶奶止不住热泪纵横。
03 巧手持家度时艰,辛勤抚育第三代我兄弟四人,大哥梦雄生于1944年6月;我是老二,生于1948年2月;老三张明生于1950年国庆节;小弟张朋生于1959年11月。
四兄弟中,只有我是奶奶亲自接生的。1947年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解放战争正在进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当时在外教书的母亲正怀着我,为了能安全分娩,她回到了婆家岭下张村。

年轻时的母亲
1948年2月2日,正是农历丁亥年腊月廿三小年夜,家家户户拜祭灶神的时刻,母亲在奶奶的帮助下,顺利地产下了我。
当时环境艰苦,所以母亲亲自为我哺乳,我其他三个兄弟都是请奶妈哺育的。
新中国成立不久,妈妈就带着我回到杭州,1950年在下城区的迎真小学(后来叫庆春路一小)恢复了她的教师生涯。
奶奶也一起来到了杭州。五十年代,我家住在下城区菜市桥边的锦衣一弄。
1954年秋的一天,爸爸、妈妈和奶奶带着我们哥仨(当时小弟尚未出生)去附近的“就是我”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
照片以西湖和保俶塔为背景,身穿西装的父亲和穿着小花点中式外衣的母亲站在后排,奶奶和我们小兄弟仨坐在前排。
照片中的奶奶身着传统老式对襟衫,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带微笑,面容慈祥,眼神明亮。

摄于1954年秋的全家福
这是我保存的照片中奶奶和我们唯一的全家福。我想,在摄影师按下快门的那个瞬间,时已75岁的奶奶心中一定充满了儿孙满堂的幸福感。
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自己的儿子媳妇都在杭州做了受人尊敬的老师,这该是多么值得骄傲啊!
六十年代初,国家遭受天灾人祸,物质非常匮乏,买什么都得凭票:粮票、油票、布票、肉票、糖票、香烟票、豆制品票、煤球票……
买菜则每户一本购菜卡,每人每天可购买一分钱的蔬菜,也不是新鲜的青菜,而是硬邦邦的花菜叶子边皮。
我家四个男孩,除了小弟张朋刚蹒跚学步,其他都是长身体的时候,特别能吃,每月二十多斤定量供应的粮食远远不够。
父亲已调到杭州师范任教,家也搬到了文二路的下宁桥宿舍。奶奶就带着我和我弟弟张明来到文二路西溪河边。

我的父亲
那时的西溪河边远不是现在这样高楼林立,河的东面是大片的桑园、荒地和池塘,野菜长得十分茂盛。
奶奶教我们一一认识了荠菜、马兰头、酱瓣草、苦菜、蕨菜、草紫、胡葱、木耳菜、猫耳朵、水芹菜、狼鸡头等许多野菜。
我们所在的文教区下宁桥宿舍,都是浙江大学、浙江教育学院、杭州师范、幼儿师范、杭州商校、外语学校等学校的教工宿舍,他们都不认识这些地里的宝贝。
奶奶带着我们,一会儿就挖了满满两大篮。回家后,奶奶把野菜洗干净,又用开水焯一下,荠菜、马兰头可以炒炒当菜吃,酱瓣草、苦菜、蕨菜可以煮稀饭或者烧菜饭。奶奶烧的菜粥、菜饭香喷喷的,特别好吃。
我在读初中,作业不多,每天下午一放学,我就回家拿了竹篮直奔河边去挖野菜,每次都满载而归。
就这样,在奶奶的巧手安排下,我家平安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还省出少量粮票支援富阳老家的亲戚。这可都是奶奶的功劳啊!
奶奶深明大义。大跃进年代,父亲要把家里的一张钢丝铁床捐给学校炼钢铁,奶奶只是叹了口气,却啥也没说,让父亲把钢丝铁床拿走了。
1966年文革发生时,红卫兵来学校家属宿舍破四旧,我家所在单元楼上共五户人家,其余四家都被抄了家。
父亲因解放前曾在学校读书时参加过三青团,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但我们家没被造反派抄家。因为有奶奶在,那年她已是88岁高龄,造反派也害怕出现意外闹出人命;另外,我家也是实打实的贫农成分,他们不好乱来。
说起我家的贫农成分,也归功于奶奶。
四十年代有一年连降大雨,山洪暴发,爷爷奶奶在胡公庙前造的石拱桥也被冲塌了。村里族人要出钱修造,奶奶坚决不同意。她说这桥当年由我家出资修建,现在垮了,理应仍由我家出钱来修。
那时我父母都在外地教书,薪水不多,也很少寄钱给奶奶。奶奶不顾众人的劝阻,毅然把仅有的一座毛竹山卖掉,换钱修好了石桥。
恰恰因为唯一的毛竹山卖掉了,土改时我家田无一分,地无一垅,毫无疑问地被划为贫农。正应了那句老话:好心有好报。

奶奶曾经捐的石桥几经修葺,已不是当初的那座桥了
04 毅然离杭回原籍,孙子得返岭下村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出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我和弟弟张明于1969年3月6日,一起去了黑龙江同江县青年庄。
同江地处黑龙江东北端,冬季气候寒冷,最低可达零下40多度。
我和弟弟还算幸运,我们下乡的青年庄,老乡都是闯关东的山东人,豪爽大度,对知识青年很关照。我是66届高中毕业生,下乡当年就当了民办老师和大队会计。弟弟与十多名知青去林场干了半年,其余时间参加大田劳动。

我(左)和弟弟在黑龙江下乡
1970年1月大队年终决算,我和弟弟扣除了预留的口粮款,还分到了一千多元现金。
这是兄弟俩生平挣到的第一笔收入,我给杭州家中汇了800元,又给了弟弟200元,让他回杭州看望父母和奶奶。
我妈妈收到汇款后给留在东北过年的我来信说:这是她这辈子拿到过的最大一笔现金。一直记挂着我们的奶奶也稍稍放了心。
1971年,弟弟张明因身体不适应东北气候,经老家亲友帮忙,户口迁回了富阳岭下张村,并于次年招工进了新建公社供销社当职工。
弟弟有了正式工作。知青点的“插友”们有的回城,有的当兵,有的投亲靠友离开了同江。我也在父母亲的要求下动了回南方的念头。
但杭州是绝对回不了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重走弟弟的老路——回富阳老家。
但回富阳老家也要个理由呀。奶奶决定,把她的户口从杭州居民户口迁到富阳老家农村。
奶奶已是94岁高龄,可谓风烛残年,但是为了我这个孙子能从北大荒调回南方,竟然主动放弃杭州的安逸生活。
于是我以老祖母年老体弱,身边无人照顾为名,打报告要求把户口从黑龙江同江青年庄迁到富阳。
经过8个来月的努力,经同江县知青办和青年庄同意,靠着岭下张村大队干部和乡亲们的帮忙,靠着我奶奶和大伯、小伯家在村里忠厚善良的好名声,也因为我父亲这个解放前全村唯一的大学生曾经帮过村里的忙,岭下张村接受了我,把我的户口落实在第二生产队。
生产队长承德伯,是大队党支部委员,也是我堂妹幼云的公公。
就这样,我于1972年10月回到了岭下张村。这也是奶奶为家庭、特别是为我作出的牺牲。

岭下张村老宅
回到故乡后,我和九十多岁的奶奶朝夕相处。
奶奶爱说叠字,夏天的老南瓜吃在嘴里,奶奶会说“甜蜜蜜”“甜津津”;深秋的竹席睡上去是“凉咻咻”“冷丝丝”的;形容冷是“凉哇哇”、“冷冰冰”,形容热是“热烘烘”、“热腾腾”……
奶奶生活经验很丰富,说:“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早上太阳很大,彩霞漫天,我去生产队干活,奶奶让我带上雨具。晌午老天爷果然变了脸,下起了阵雨。
夏天雷雨很多,闪电也多,奶奶说:“东闪风,西闪空,南闪火门开,北闪有雨来。”
这种凭着观察闪电的方位来预测天气的办法,我曾经屡试不爽。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奶奶教我做人的道理。
因为父母硬性要求,我回老家后没有马上去公社当民办老师(文革期间像我这种1966年毕业的老高中生真不多),父母要求我在生产队劳动。
我每天跟着社员们上山伐竹砍柴,挑担种地,很累。在黑龙江干活都是一马平川的黑土地,而富阳老家都是山,砍下毛竹后还必须把毛竹从山上背回村里。
山路崎岖,空手上山下山都战战兢兢,提心吊胆,还要背毛竹、挑担子。别的壮劳力一次可背4株大毛竹,我只能背2株小的,所以工分很低,内心不免消沉。
奶奶看在眼里,给我讲爷爷当年起早贪黑勤奋干活的故事,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古训激励我,一边悄悄给我增加营养,变着法子给我做点好的。她自己经常吃番薯,让我吃白米饭。
奶奶常说,“梅花香自苦寒来”,鼓励我多看书,向父亲学习,争取将来也成为大学生。

老宅的楼梯
看到我在楼上静静看书,奶奶很欣慰,会悄悄地给我端来一杯茶水。
父母亲按时给我和奶奶寄来生活费,奶奶很节约,一分钱也舍不得乱用。但是亲友们若有事相求,或是需要借钱救急,奶奶总是慷慨解囊。
她常说做人要乐于助人,要学会感恩,爷爷去世后她孤儿寡母艰难度日时,亲友、邻里都热情伸出援手,所以能帮人时一定要帮。
奶奶待小奶奶王氏就像亲姐妹,俩人数十年间一直以姐妹相称,从未红过脸。
奶奶与我大伯、小伯的关系也十分融洽,视如己出,对我的堂弟尧新、堂妹幼云、杏照、杏芳都疼爱有加。他们也都非常敬重奶奶,奉为家长。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奶奶一生忠厚善良、乐于助人,她的待人处世,就是给我们最好的教育。
1973年春天,我在表哥史培基先生的推荐下,被招进新建中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奶奶很高兴,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好好教书,做个耐心、细心、有爱心的好老师。
05 九五高龄辞人世,五天预测准如神新建中学在公社的所在地虹赤,离岭下张村有近10里地。
1973年10月下旬,我回到岭下张村看望奶奶。平时奶奶总在楼下堂前闲坐聊天,但那天我没看见她。
小伯、小婶婶告诉我,奶奶说她有点不舒服,休息去了。我上楼进了奶奶的房间,只见她躺在床上,面色有点苍白。
我问奶奶哪里不好。她说小毛病,只是肚子有点不舒服。我说送她去公社看医生,奶奶不肯去,说自己一大把年纪了,不想折腾。
第二天是星期一,我一早要回到虹赤新建中学上课。临行前我去看奶奶,再三请她和我一起去公社卫生院。
奶奶这时和我说,让我给爸爸妈妈拍一封电报,叫他们回来一趟。我急了,问她还有什么吩咐,奶奶伸出一只手,张开五指摇了摇,说不要紧,她还有五天好活。
我拿出几片药请奶奶服用,奶奶摇摇手,竟是不肯。
我心急如焚,离家直奔公社。我向学校请了假,到公社邮政代办所给父母拍电报,电文只有六个字:
“祖母病危速来。”
父母当天晌午收到电报,马上分别向单位请了假,直奔富阳。
父母先后换乘了三辆车,才赶到富阳县城,但午后到达汽车站时,开往常绿公社的客车已经开出。
父母赶到中埠准备改乘渡轮,却被告知,到春江的渡轮当天已经停运。父母万般无奈,只得回到富阳县城,在旅馆住了一宿。
第二天,父母一早乘车先到虹赤,再步行10里路,才到了岭下张村。
奶奶见到我父母,很是欢喜,精神也突然好了很多,拉着手说长道短,似有说不完的话。这一天是星期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霜降。
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奶奶在史家山的女儿,在萧山尖山下、斜爿坞和常绿姚村的外孙、曾外孙,以及各地的亲友,纷纷闻讯赶来看望奶奶。
奶奶和他们一一打着招呼,谢谢大家的探望,还和我姑妈她们聊起了陈年往事。
父母让奶奶好好休息,少说话,但奶奶变得像个任性的孩子,全然不听劝阻。
星期六午饭后,学校放了假。我和堂妹夫张海校拉着一车大米、油盐酱醋、蔬菜豆腐、还有在公社供销社工作的弟弟设法买来的猪肉,从虹赤回岭下张。
海校长我一岁,是新建中学的负责人。他推着独轮车,我在前面拉。
从虹赤到岭下张村,是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全是上脚路,300多斤重的米和菜,累得两个教书先生汗流浃背,路上歇了好几回。下午三点多,我们才到达“鸦雀窠”。
奶奶12年前生过一场病,后来不治而愈,只是堂前养着的兔子死了一只。奶奶属兔,同住在祖屋的大伯、小伯和小婶婶都说,奶奶心地善良,所以那只兔子抵了奶奶一命。
12年过去了,奶奶已是95高龄,可谓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朝不保夕。我内心充满了忧虑,因为五天前,奶奶曾亲口告诉我,她还有五天。这一天,正是奶奶和我说过的第五天。
晚饭时,我和父母端着一碗薄薄的米汤到奶奶床前,要她喝。
奶奶不肯,在我们的再三劝求下,喝了两小口。
我与父母还有姑妈等环守在奶奶床前,又聊了好一会儿天。奶奶出奇地冷静,要求我母亲和姑妈帮她洗了脸,换上一身新做的藏青色的布衫和长裤,又帮她把一双她亲手做的新鞋,穿在小脚上。
这时已到了三更天,她对周围的亲人们说:“你们陪了好几天,都累了,谢谢你们,大家都休息吧,我也要睡了。”
奶奶用那双总是那么明亮的眼睛慈爱地看了看我父母和大家,安静地闭上了双眼。
不一会儿,奶奶就安然离开了我们。
奶奶走了,走得那么从容,那么安详。
老人家知道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就像知道一盏油灯即将耗尽最后的一滴油一样,预测得分毫不差。
这一天,是1973年农历十月初二,阳历10月27日。奶奶走的时刻,天上没有月亮,星光惨淡,山风阵阵,溪水呜咽,像是老天爷也在为她送行。
第二天我们就送奶奶上了山。奶奶的墓穴是她生前就选定做好的,就在小黄岭下的茶园家。
奶奶的坟墓西南朝向,正对着我家的祖屋。从那里望下来,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家的祖屋。
出殡回来的中午和晚上,亲友们聚在一起吃豆腐饭。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奶奶一生忠厚善良、品德高尚、乐于助人,而且高寿,来吃豆腐饭,既是对逝者的敬重,又能分享福气。
长者们有的讲起了我奶奶的两次出资造桥,有的讲起了奶奶培养出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也有的提起了奶奶曾给予的帮助。
奶奶赢得了广大村民的敬重和爱戴。哪怕是最后离开人世,她也要施人恩惠,给人快乐。
奶奶去世一年后,我父亲落实政策,重新当了教师。母亲于1975年光荣退休,根据当时的退休抵职政策,我于1975年的10月进杭州武林中学当了一名公办教师。
1977年恢复高考,我有幸考上了杭州大学中文系。
在古代文学课上,我读到了晋代李密《陈情表》中的句子:
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
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
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我不禁引起内心深深的共鸣,潸然泪下。
是的,如果没有奶奶含辛茹苦培养我父亲去外地读书,父亲就不可能认识我母亲,也就不会有我们兄弟四人;
我出生时,如果没有奶奶亲自为我接生,母亲生我就不一定会那么顺利;
困难时期,如果没有奶奶的巧手安排,我们兄弟四人很可能早就瘦得皮包骨头,没有现在的良好身体;
文革中,如果不是88岁高龄的奶奶在家,我家也很可能难逃被“造反派”抄家的厄运;
如果不是93岁高龄的奶奶放弃安逸的杭城生活,把户口迁到富阳农村,我就不能从东北迁回富阳,后来也就未必能顺利参加高考……
真是:“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 我受了那么多奶奶的恩泽!
奶奶从小就教育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诚实为人,勤勉做事。
我没有让她老人家失望。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成了家乡第一个大学教授和浙江大学博士。奶奶地下有知,当含笑九泉。

金庸先生来访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如今,我也已年纪七十,成了两个孙女的爷爷。含饴弄孙,抚今追昔,不由更加怀念奶奶,回想起奶奶昔日的谆谆教诲和亲切垂训,内心百感交集。

我与董建华先生
今天我写作此文,既是告慰先辈,也是为了寄托深情与哀思,让子孙后代追远怀亲,传承善良、淳朴、勤劳和乐于助人的家风。
历经百年风雨,岭下张老家的祖屋日趋破败。我们几个兄弟商量后,决定对老屋拆除重修。
我要经常回到这里住。呼吸着山里清新的空气,我格外满足。这是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和兄弟们的家。
我生于斯长于斯,我人生最美好的情感和回忆在这里,我的根在这里。

修葺前的老宅
丑丑·后记张老师:助人为乐,自得其乐
张梦新老师是木木(林煜)的大学老师。
常听木木讲,张老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一生严谨治学,爱学生如子女。
如今,木木已人到中年,亦常常念叨张老师为师为人的点点滴滴,人品师品都是我们的榜样。想起,便打电话给张老师。
于是,深秋时节,张老师背着双肩包从杭州城西辗转两趟地铁,一个多小时赶到城南的“丑故事”。
张老师已是古稀之年,依然笔耕不辍,到处奔忙,助人为乐。
看到张老师写奶奶的文章,我们都感动不已,终于知道,为什么张老师会长成今天的样子。为什么,张老师这么乐于助人,原来皆因家风渊源。
我们提出,想去张老师的富阳老家看看,拍一些照片。
周日,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气温骤降。张老师推掉所有的工作,一大早坐地铁赶到城南,早早地等在地铁口和我们汇合。
岭下张村,张老师出生成长的地方,四面环山,一条溪流穿村而过。
窄窄的道路两旁都是高大的乡村别墅,车子行到尽头,一转弯又是一方开阔天地。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张老师说,这个村民风淳朴,路不拾遗,自建国以来,没出过一起刑事案件。
到了真正的路尽头,再沿着长长的台阶爬到高处,就是张老师的家。房子背靠将军岭,面对小黄岭。小黄岭那边就是萧山地界了。
张老师的弟弟正好从杭州回来住几日,听说哥哥要带学生回来,在厨房里忙了半天,烧了一大桌菜。
张老师拿出刚刚修订过的张家族谱给我们看,厚厚一叠,可见张氏一族枝叶繁茂。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仲夏,族人推举张老师的父亲张麟祥为族谱写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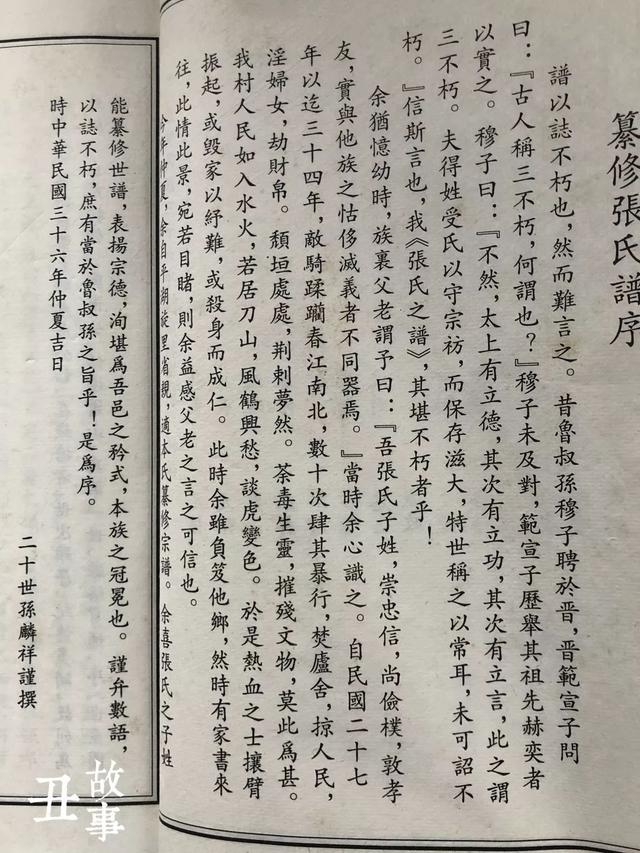
张老师父亲张麟祥作序
六十年后,族人又推举张梦新老师为族谱写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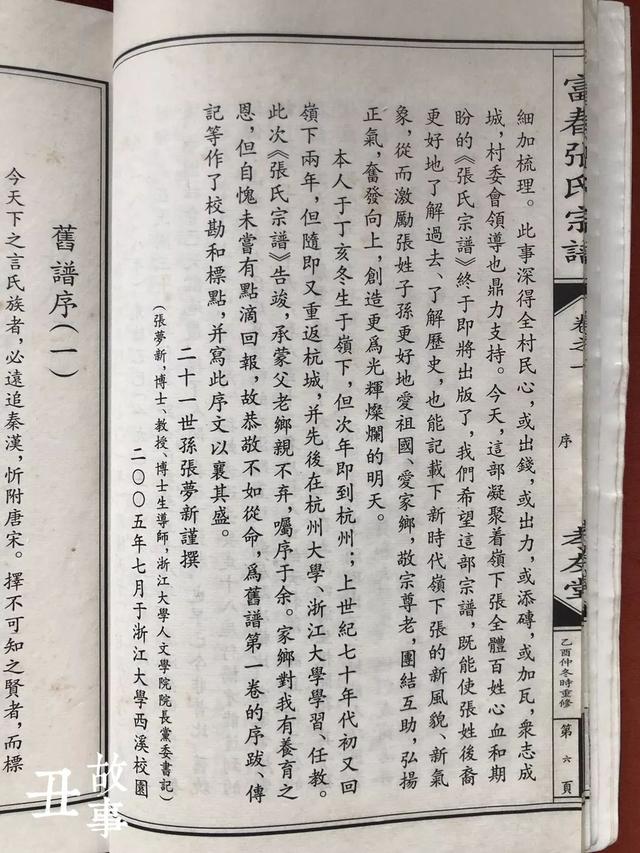
张梦新老师作序
张老师说,父亲曾告诉他,八个字世代铭记:助人为乐、自得其乐。
张老师和弟弟们也是如此行事,兄弟姐妹相亲相爱,互敬互让。乡里乡亲,遇到谁有困难,他们总是义不容辞尽心尽力帮忙。
村民看到张家门开着,常常摘了菜送上门来,表达自己的感谢。
我们去拍奶奶曾经捐过桥的地方,张老师领着我们在雨里上坡下坡,给我们讲每个地方的故事。他深爱这方山水,并以此为傲。
张老师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一生成就斐然,却谦逊低调,淳朴善良,广行善事,处处乐于助人,而不张扬。
回杭路上,张老师执意不要我们送他,只要我们把他放在路边,让他自己坐地铁回去就好。
我们怎么好意思就把他扔在路边,自作主张径直把车开到了城西。
快要到张老师居住的小区了。张老师又开始念叨,反复要求我们把车子停在马路对面,他自己穿过马路进小区就得了。
我们还是没有听张老师的,左拐把车子停到了小区的正门口。天空中又下起了小雨。
这回,张老师执意要下车自己走,再也不肯让我们送他进去。张老师就是这样,宁可别人麻烦他,也不要麻烦别人。
这是祖辈相传、发自肺腑的淳朴、真诚和善良。
-END-
原地址:https://chinesefood8.com/43167.html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